[今日主題曲]
(是日專用字色 #890604)
 (蘋果 / 都是那些日子)
(蘋果 / 都是那些日子)
關正傑《一點燭光》
作詞:鄭國江 / 作曲:陳秋霞
盼可將燭光交給我 讓我也發光芒
寒流裡 願同往 關心愛心似是陽光
我的心一般奔放 願挺起我胸膛
如能以熱和愛 自能導出心裡光
淒冷中 望星與月也寒 我但要燭光照亮
誰願意 步向康莊 誰亦要 走走看看
盼共你 結伴去 以心中暖流 和風對抗
(剛剛想起,紅星學生帶領港大學生會投共第一步,就是出了個和風閣呢……)
為了替同事找推介的書,結果當然又是買了一堆。有些歸圖書館,有些歸我。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Michael J. Sandel著,吳四明、姬健梅譯,台北﹕先覺,2012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Michael J. Sandel著,吳四明、姬健梅譯,台北﹕先覺,2012
其實之前已買了《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和《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放在學校,難得前者也有幾個人借過(後者未留意),但在下還沒時間拿來讀(其實連那段片我也沒看完)。既然讀書會下次很可能講這本,所以乾脆買了這本,和借下《正義》快快讀。
其實單是《錢買不到的東西》這個名字就值得推介每天被中環價值荼毒的香港學生讀吧﹖
 《擦擦史:一部關於溫柔呵護我們胯下的輕薄好夥伴─衛生紙的趣史》(Bum Fodder:An Absorbing History of Toilet Paper) Richard Smyth著,蔡宜真譯,台北﹕商周,2013
《擦擦史:一部關於溫柔呵護我們胯下的輕薄好夥伴─衛生紙的趣史》(Bum Fodder:An Absorbing History of Toilet Paper) Richard Smyth著,蔡宜真譯,台北﹕商周,2013
這本其實令買了《大便書》的「變態」方某人很頭痛,究竟應該留給自己還是放在學校﹖
最後我決定這次放在學校,我想他們會對「未有廁紙之前大家用甚麼」有興趣吧。
 《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Gordon Mathews著,Yang Yang譯,香港﹕青森,2013
《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Gordon Mathews著,Yang Yang譯,香港﹕青森,2013
為何要買這本,應該沒疑問吧﹖通識科的課題有「全球化」又有「身份認同」呀,重慶大廈不就是這兩個課題的焦點舞台嗎﹖
 《法醫才看得到的人體奧祕》上野正彥著,陳嫺若譯,台灣﹕如果,2012
《法醫才看得到的人體奧祕》上野正彥著,陳嫺若譯,台灣﹕如果,2012
方某頗喜歡上野正彥的《聽聽屍體怎麼說》,所以一見到作者名字就立即拿起來。不過內容其實是生理學知識居多,法醫只是順帶一提,所以留給學校好了。
 《香江有幸埋忠骨》丁新豹著,香港﹕三聯,2011
《香江有幸埋忠骨》丁新豹著,香港﹕三聯,2011
書本身包起了,見到丁新豹三字才敢沒看過內容就買。何況封面也把書的內容表達得很清楚﹕就是葬在香港墳場、跟辛亥革命有關的人物傳記。
(或者,我潛意識是故意在這個時候買這種書的。)
 《萌える!思想主義一本就讀懂:將63種著名主義擬人化!》吉岡友治監修、YOSHIOKA YUJI作,高詹燦、劉淳譯,台灣﹕瑞昇,2013
《萌える!思想主義一本就讀懂:將63種著名主義擬人化!》吉岡友治監修、YOSHIOKA YUJI作,高詹燦、劉淳譯,台灣﹕瑞昇,2013
很明顯是買給學生看的。近年日本人甚麼都拿來萌化的作風,萌化論語我都頂唔順,不過如果說那些「乜乜物物-ism」經常在傳媒出現但學生不大了了,那麼找本書吸引他們看點簡單的介紹,也不錯。
--------------------------(以下是私伙的分隔線)--------------------------
 《帝國:大英世界秩序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Niall Ferguson著,睿容譯,新北﹕廣場,2012
《帝國:大英世界秩序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Niall Ferguson著,睿容譯,新北﹕廣場,2012
(這位譯者的名字竟然只能在預行編目才見得到,出版者好像覺得是不值一提般,很不尊重。)
大概好像只在《新國富論》看過對殖民帝國的整體評價。英國這個最大殖民帝國,有趣在於非常「地方智慧」,比其他帝國都更樂於放手給總督因地制宜管治。這段歷史對我們其實很有用。
 《鐵路大比較》川邊謙一著,薛智恆譯,台北﹕台灣東販,2012
《鐵路大比較》川邊謙一著,薛智恆譯,台北﹕台灣東販,2012
主要是為了看鐵路系統、路軌和訊號那部分。份量其實不多,還是想起小時候看光復科學圖鑑鐵路篇的時候,總是很喜歡訊號那部分。如果有人寫本通俗向的書,專門介紹各種鐵路訊號就好了。
 《日本家徽圖典》,丹羽基二監修、鈴本亨等著,黃碧君譯,台北﹕商周,2008
《日本家徽圖典》,丹羽基二監修、鈴本亨等著,黃碧君譯,台北﹕商周,2008
其實買這本是因為下面那本﹕ 《完全圖解戰國武將家紋軍旗事典》大野信長著,孫玉珍譯,台北﹕遠流,2011
《完全圖解戰國武將家紋軍旗事典》大野信長著,孫玉珍譯,台北﹕遠流,2011
邦少買了一本,然後我看頗有趣(方某向來對旗幟徽號之類有興趣),於是有次特價買了。
不過那本充其量只介紹武將的家徽,《日本家徽圖典》卻不是旨在武家、更不是哪一家,而是解釋日本家徽裡的元素。更合在下所需,所以買了。
[馬來西亞大選之繼續推文轉xanga]
mkini_cn﹕ 林吉祥:不要种族化人民抉择 轰蔡细历论述背叛大马人愿景 马华总会长蔡细历在该党惨败后,指称本届大选成绩形成两种族制;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即刻驳斥蔡细历言论,呼吁后者不要种族化人民的抉择。... http://fb.me/2C2PxaLen
ivansyli﹕ fw: 澳門人,如果你覺得大馬選舉很黑暗的話,我抱歉要告訴你,澳門立法會組成更黑暗。下屆多達58%議席並非透過普及而平等原則選舉產生,當中有7席更加是由特首直接安插,連選也不用。 -但, 香港人不知幾羨慕澳門有錢派喎! 好多人話想移民/入籍/拎身份證添呀! 何謂核心價值?又一例子
aac_ 17h﹕ 一些支持民联的马来西亚华裔说,如果民联获胜,他们认为会出现暴乱,毕竟国阵执政多年第一次失败,他们不会善罢干休,已经传出多地发生了打架,他们今晚会提早回家。一些开店的华裔虽坚持营业,也说如果得知民联即将获胜他们会立刻回家。但即使如此他们仍不惧危险投票给民联
ivansyli﹕[民主是個好東西] 即係,民主既"可貴"在於,就算你執政者想出術,其實都要分好大氣力,特別係而家資訊咁發達,冇以前馬可斯咁簡單. 況且,就算個莊冇換,都或多或少問左責.上次大選國陣都已經換左人,納吉先有得上位. 今次一樣,就算納吉繼續坐,至少都可以迫佢做到d野,唔可能隻手遮天
fongyun﹕其實沒甚麼等不等下次,就算沒贏到國家政權,也夠震散國陣的了(馬華輸到不敢入閣)。學 @ivansyli 話齋,政權不易手不改變(typo:代表)選票不會帶來改變,連馬來人也開始離棄巫統,納吉不敢再走種族政治路線了。
SinChewPress﹕ 已再度執政中央的首相拿督斯里納吉宣佈,在未來的4、5年內,國陣將會棄除種族性與極端宗教的政策,以贏取人民的支持。
28481k﹕ 香港台灣大馬新加坡共勉之。 QT @kenworker: 一覺醒來,一切如昨。見大馬友人寫道,「接下來五年,要鍛鍊身體,健康生活,鬥長命。」是的,長命最重要。也別忘了再來台灣,互相取暖啊。
(答陳牛問—cowcfj﹕ 馬來西亞政治真奇怪,國陣主要是由單一種族的政黨組成,大家利益不一樣究竟是如何組成聯盟的?)
fongyun﹕ 簡單而言,分而治之,根本直接學英國人在殖民地的招數嘛。巫統是領導黨,但找一批不同種族的代表去「以華制華」「以印制印」,向少數「族裔領袖」分權分利換取馬來人優先政策不被挑戰。更何況馬來人優先本來就只是個給權貴分利的幌子。
fongyun﹕ 沒關係,只不過是因為英國人在香港也是一樣做法,只不過這邊的特權分子叫新界原居民。有留意一些討論英國殖民地歷史的書就會發現他們在很多地方都這樣做,印度和非洲都一樣。
fongyun﹕ 與其說(中共)高明,倒不如說這次選情已出乎國陣意料之外了。單講種票大馬都有做,而且種得更大規模。 RT @makarat 共匪喺香港選舉嘅種票技巧比馬拉政府高明得多。喺香港,唔需要去到停電搬選票呢一招,親共建制派都會大贏特贏。
fongyun 原來民聯贏了首都外圍的雪蘭莪州,真正包圍中央 ![]() http://www.stasiareport.com/asiareport
http://www.stasiareport.com/asiareport
(註﹕其實上屆已贏了,今屆連勝。)
fongyun﹕講黎講去都係選舉公義而非華人問題,又何來沙文主義﹖(當然香港傳媒就差好遠,CCTVB竟然說這次選舉華人是關鍵——你自己都識講大部分華人支持反對黨,咁仲有咩懸念﹖梗係要睇馬來族投票意向﹗)
fongyun﹕其實我都係抄,睇多少少東南亞政治分析都會知道華人一向不滿國陣,一向支持國陣(或者應該說被巫統種族政治騎劫)的馬來族投票意向才是關鍵。所以CCTVB如果不是出於自我中心就是無知到連這些分析都沒看過。
fongyun ﹕「至少我都冇醒起呢個咁明顯既虛妄」-->因為香港始終係華人佔絕大多數,好多時對呢D華人中心觀點係冇乜警惕。睇多D東南亞政治新聞就會知人地好避忌呢D野。
fongyun﹕其實CCTVB咪又係果種「中國崛起我地威晒」心態(所以華人在外國選舉「一定」好關鍵,話之美加定大馬),上次連港台拍華人移民史都有少少呢種味道。完全唔知南洋華人經歷多次排華,幾鬼避忌「中國認同」。
fongyun﹕馬華公會聲稱有「華人海嘯」添,佢地都多餘,華人傾向反對黨根本不是這幾年的事。如果說香港人這樣說是華人中心,馬華這樣說是黨派老化到完全脫離現實。
fongyun﹕其實我認為近年反對黨成長最大的關鍵,是走出了國陣主導的「族群政黨模式」,開始跨種族了。要有「一個馬來西亞」,根本不應該再以種族區分政黨。這次不幸是還未能吸引足夠的馬來族票源,但改變已經開始。
在紐倫堡很忙的(要找辯護律師嘛  ),所以也沒時間看書寫文。碰巧前幾天跟網友在推上討論自由市場和政府介入的問題,覺得有點意思,值得把部分內容抄過來保存。
),所以也沒時間看書寫文。碰巧前幾天跟網友在推上討論自由市場和政府介入的問題,覺得有點意思,值得把部分內容抄過來保存。
Isumi_MOD﹕ 其實這是政府失靈。要拆很簡單,建新碼頭或定期招標制造競爭就可以了。可惜政府不敢做。整個情況其實就是地產霸權的翻版,即最根本的供應在政府手中,但政府不敢/不願提供競爭環境,結果造成壟斷
tinthefatty﹕ 我估真正市場主義者只會覺得工人罷工係市場現像。吾妻昨日同我講話佢有個小六學生話班工人讀書少所以賺錢少,唔應該貪心更唔應該罷工,佢話佢有睇電視,明白整件事,東將(張)西望都係咁講云云。我估今日吾妻同嗰班同學傾傾呢件事。
fongyun﹕ 超,佢依家唔機械人化只不過係因為將「人」的工資同工作環境壓低到連機械人都不如之嘛。
chenglap﹕出口導向的社會基本上經濟建基於別人需要你的出口產品或服務上, 但如果世界已經很發達, 很可能就會導致根本就沒有任何需要的出口, 一個富足的世界最多的就是熱錢.
chenglap﹕有沒有價值是一種動態的狀態, 舉一個例子說, 一個核子科學家在清朝, 價值是零, 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能力發展核子科學. 所以那個核子科學家可能還是要耕田. 但耕田卻只能發揮很低的價值. 產業經濟的停滯有很深遠的影響.
chenglap﹕「不惜一切幫助工人就業(包括使用補助)」和「全民失業救濟」是解決問題的兩個不同的方向, 但兩者都會有人反對的, 前者會被認為是扶植沒競爭力的產業, 後者則被認為是養懶人. 但產業自身無法升級是問題的源頭.
chenglap﹕轉行這件事在越現代化的社會就越沒有可行性, 比方說, 現在市場流行寫 ruby of rail, 我總不可能叫那些碼頭工人跑去學 RoR, 轉行當程序員. 市場需要醫生, 也不可能人人當醫生.
chenglap﹕必須要怪別人, 而且政府絕對有責任. 在自由市場中, 政府本身就是要處理市場無法完成的問題. 否則產業停滯, 社會動盪, 被競爭拋離, 最終導致整個系統的瓦解. 政府, 本來是受薪地處理這問題的組織. 清朝就是例子.
chenglap﹕不應該單純歸究於「這是現實」我們就可以當作他是必然會發生的, 而是這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一個核子科學家轉職成農民, 是一種社會的損失. 對這種問題視而不見, 才是一種家裡蹲的邏輯對吧?
chenglap﹕那個社會最終會自然崩潰, 陷入混亂, 歷史已顯示如此. 而這個問題製造了底層的悲慘. 當然, 我們可以堅持這並不是問題.
chenglap﹕心態是結果, 極右和極左都容易從阿伯身上產生就是如此.
fongyun﹕行業消失如果純粹能是因為沒人需要,這固然無法保留(或者只能當「文化財」少量保留)。但香港的情況只是因為很多行業的產出追不上不斷飛升的租金,而不是因為沒人光顧。
AnthonyKuuga﹕當政府插手市場就不是單純解決市場處理不了的問題,而只是以第二個問題去轉移了第一個問題。我認為兩者沒甚麼錯對,兩者都不完美,只是最終得益者有所不同吧了。
chenglap﹕政府是否插手市場我認為這是很主觀的, 基本上連治安(警察), 教育, 住房, 都是市場的一部份.
chenglap﹕我不打算這樣說, 但如果說政府干涉市場就是罪, 那麼到底有甚麼東西, 是不能市場化? 總需要有個定義和界線吧? 如果定義就是「現在政府在做的就不是市場」, 那就變成循環輪證了.
chenglap﹕房地產本質上已經是難以拒絕的, 你的生活和工作, 基本上無法脫離房地產. 無法拒絕不等於不在市場當中, 「自由」市場從來都有很多強迫的部份.
chenglap﹕所以不能拿 google 當例子, 因為他明顯是建立在政府之前的鋪路上. 民營的資金明顯地, 難以支持像核融合這種長達百年, 在投資者有生之年無法商業化和盈利的研發.
chenglap﹕僱傭兵代表武力可以市場化, 公權力只是代表他拿錢的權力, 他拿了錢之後可以從市場購買任何東西, 包括僱傭兵, 跟買文具一樣. 這意味著「武力不能市場化」這點並不成立.
chenglap﹕至少我不接受說, 用「政府干涉市場就是萬惡」為理由, 去阻止政府投入像科研或者開發新產業這樣的工作, 特別是市場明顯失能時.
chenglap﹕怎樣控制撥款的人, 是控制公權力的問題; 這就像武力一樣, 政府也可以用武力隨便殺害不順眼的人, 這跟使用警察的權力是沒有分別的.
chenglap﹕我並不是主張大政府, 但是我也不同意認為政府甚麼都不必做, 市場就能解決一切問題的塔利班式原教旨新自由主義.
chenglap﹕市場本身就會製造很多的副作用, 包括了賺錢的產業壓縮其他產業的生存空間, 例如房地產業導致整體成本的上升.
chenglap﹕我是認為這裡的問題全是雙重標準, 一方面政府提供教育, 住屋, 在自己認同時就不算干涉市場. 而自己覺得沒必要時, 干涉市場本身就已經是罪名.
chenglap﹕這個就是雙重標準. 教育, 房地產, 就是特定的產業, 也需要投資. 你覺得有必要, 也有人覺得沒必要. 認為政府根本不應提供公屋的人大有人在.
chenglap﹕我認為兩者都是必要的, 你是憑甚麼看成是為了科技去排除了教育? 況且打從一開始, 教育本身也是不知道有沒有效益. 這本則上就是根據個人愛好的雙重標準.
chenglap﹕原初的社會契約論, 例如 Thomas Hobbes, 認為人類有一切自然權利, 而自然權利包括殺人, 社會契約, 就是建基在放棄部份自然權利上. 跟現代的人權是沒甚麼關係.
fongyun﹕我根本就認為政府是市場的一部分(土地市場就是明顯例子,批評政府干預土地供應根本是胡說八道),只不過它通常是以壟斷者的形式出現。
nuochan﹕那麼所謂市場主義者便宜得很,一有好事就是自由市場的功勞,一有壞事就是政府的過錯。但是市場會不會為荒山野嶺的居民修路、通電、架電話線呢?他們是不是因為投胎的地方太偏僻,所以就不配享有基本的醫療服務呢?
28481k﹕其實,這個稻草人是你們libertarian種出來的。
fongyun﹕其實稅收和福利已是經民意授權剝奪某些人的財產給另一人。
fongyun﹕無論政府「做」或「不做」某件事,在市場上本來就會令某些人獲益。等於假如說不想增加碼頭益了某公司,也只不過等於益了HIT。你以為政府可以選擇「不介入市場」,但我認為根本沒這個選擇存在。
fongyun﹕所以我要強調的是,你說的問題其實只是「量」多與少的問題,根本不是「質」有或無的問題。行業扶持也是一樣,就算為了推動全社會發展,你也可以要求限制於最低程度。
事實上,所謂的自由市場從來就不真的自由,而政府的有型之手亦從未離開過。
(更不用說,經濟學家可以用excel計錯一行數得出錯誤結論……Alone in the fart結論是「認錯真的很難」。)
------------
另附送對琉球某日本華文推友的回應﹕
fongyun﹕琉球的「中」和「外」是甚麼意思﹖這樣解太牽強,因為中國官員不會用「中」稱呼琉球的某部分,有「天朝」意識的他們只會自視為「中」。至於「閩山盡處」只能說是離開了閩省(福建省)的管轄範圍,不等於國界。
fongyun﹕第一點是想當然矣,不受省管轄不代表就不是國土,美國有些領土也不屬於任何一州。第二點是誤讀,那句只是說中山在琉球中央,當然沒錯,但文意跟「中外」那句有別。第三點,聽聞是沒問題的,因為這反映了當時中國人對中琉界線的看法。
fongyun﹕如果要鬥首先發現,琉球是一定不比中國早的。正如井上清著作所指,琉球人稱呼釣魚台列島都是用中文名或接近中文名,日文尖閣反而是襲自英國人的命名。當然,你可以質疑中國人先發現但未必有實質管理,這點井上清反駁過但至少法理上你們可以質疑。
fongyun﹕不懂日文,不知道版面跟「中外之界」的解釋有何關係。當然我看得出有部分是指稱中國歷史上有其他聲稱未到釣魚台已出國境的說法。我同意一點是中國古代對「國土」的看法並不會有現代國際法要求的那麼嚴謹。
fongyun﹕第一,因為你用現代國際法的觀念去看古人的文獻。嚴格來說藩屬國並不是清朝的領土,正如清朝沒說過朝鮮是中國領土,朝鮮是屬國。這些關係無法套進現代人的概念之中。
fongyun﹕第一點(續),至於省之外,清朝還有將軍領地,滿人發源之地一直到光緒朝之前都是由將軍管轄沒有「省」可言。當然我不是說釣魚台設了將軍管轄,我甚至認為中國人因為這些是無人小島所以漠視了。但中國人先發現並製圖以供巡邏之用證據甚明。
fongyun﹕第二,我不是說「中外」那句文意「特別」,而是說它跟你引的那句文意不同。你引的那句因為已說明了主語是琉球,所以「中央」以琉球為主沒有問題。但如果沒有特別指明的話,古人說「中外」的時候,通常就是指本國與外國、或中央朝廷和地方的對比。
第二次讀書會,主題是「直接行動」。方某認識不多,只找了兩本薄書﹕


《直接行動》葉蔭聰,香港﹕進一步,2010
《公民抗命》丁若芝,香港﹕進一步,2003
這次請了兩位嘉賓分享。方某了解不深,只能簡介,有心人可繼續探索。
第一位是 Galileo,主要分享了幾段影片。不過核心環繞一幅圖﹕
 (Tree of the "Theater of the Oppressed")
(Tree of the "Theater of the Oppressed")
Theater of the Oppressed 據聞是一個劇作家提出的理論,認為劇院和民主應有關係。古希臘的悲劇傳統只是消磨了受壓迫者的意志,讓觀眾以為自己投入了角色但其實只是旁觀者。這個理論主張把觀眾轉化為演員。
香港是一種 culture of disappearance,好像是對自己的歷史、經驗和文化不屑一顧任其消失。例如當年蘇守忠和吳仲賢的抗爭經驗,因為他們不是主張,所以被有意無意的忽略了。(碰巧,當天有人邀請了吳仲賢的長子到會旁聽。)
如果套進圖裡的大樹,香港的這棵大樹,其實無根。有很多根源的東西需要回顧,才能長出健康的大樹。
Galileo 播了幾段片。
1. Dr. Strangelove 的結局,當開場白。正如戴耀廷自稱,佔領中環如同核彈,那麼是否會變成一部 doomsday machine﹖
2. 1992年把日本作品改編電影《妖獸都市》,隱喻了香港人對九七年大陸入侵的憂慮。由於拍得頗奇怪,成為一代cult片。
3. 許鞍華的《千言萬語》,正是以七八十年代的社運人為藍本。甘浩望神父,吳仲賢、長毛(的角色)都在片中出現。後兩者因為是托派,同時受左右兩方忌憚冷待。現在很多人認識長毛,也不一定知道他當年做過什麼事。
4. 笑片《救世神棍》,重點與其在警惕神棍,倒不如說在於大家要反思自己參與社運,是否只是像片中那些盲信者求贖罪、解除自身不安的行為﹖消費了運動之後又帶來了甚麼﹖
5. 英國 Channel 4 電視劇《Black mirror》﹕最受歡迎的政治人,可能是個虛構人物,因為他沒有背景、沒有陰影、沒有黑材料,隨時可以套上不同的政治主張,自然可以吸引最多支持者。我們現在的政治,又距離這樣多遠﹖
第二位是周澄,介紹了三本書。
 《廢棄的生命》(Wasted Life) 齊格蒙特‧鮑曼,谷蕾、胡欣譯,江蘇人民,2006
《廢棄的生命》(Wasted Life) 齊格蒙特‧鮑曼,谷蕾、胡欣譯,江蘇人民,2006
(圖取自博客來)
討論全球化帶來的「人口問題」。作者認為移民、難民這類現象為全球化所衍生,本身就是社會製造出來的「問題」,但社會卻往往只想逃避、不負責任,就像我們對待文明社會製造出來的垃圾一樣。
周澄表示是參與人口政策關注組時留意到這本書,當「雙非」之火蔓延,連港人所娶的「單非」也受牽連的時候,很多人沒留意透過「專才計劃」一季也輸入了三四千人。那些人又是否這個社會需要的呢﹖準則如何﹖社會似乎沒討論過。
《大志未竟》,吳仲賢的悼念文集。對這個托派,大眾媒體自然沒甚麼興趣,所以書也是朋友合作出的。當年的「火紅時代」,現在只被歸納為「社會派vs國粹派之爭」,只因為這兩派的人後來都有升官發財的,身處邊緣的托派自然成為一段被遺忘的歷史。
現在回望,周澄認為現在社運似乎在回應歷史。當年失敗的東西,到社會有需要、有氛圍的時候就容易做到。與現在網上很流行的失敗主義或犬儒批評相反,我們未必需要勉強一定要達成什麼。(方按﹕孔夫子的「義之與比」﹖) 有時成果不一定是當日就見到,而需要較長日子才會萌芽顯現出來。現在很多不同的路線和做法,雖然彼此道有不同,但可能殊途同歸。實不必為一些品格上的問題糾纏。
對於這點,倫爺有質疑。這種司徒華式的「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思維,往往令搞手怯於更向前走一步。一場運動可以不計成敗,但搞手不應不計成敗。因為搞手要向群眾負道義責任,應該是謀計最大成功的可能。
(倫爺提出的例子是民陣。雖然對民陣的批評在下實有保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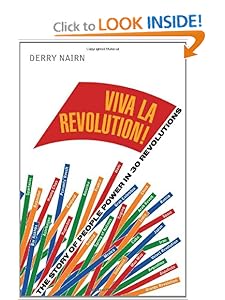 《Viva la revolution!: The Story of People Power in 30 Revolutions》Derry Nairn. Elliott & Thompson, 2012
《Viva la revolution!: The Story of People Power in 30 Revolutions》Derry Nairn. Elliott & Thompson, 2012
近年中東的茉莉花革命,可能令大家懷疑「革左又點」。英國歷史學家回顧史上三十次人民起義的故事,模式不見得都一樣,有成有敗,但影響同樣及於日後。(有篇中文介紹)
問答時間,除了上面提及倫爺的質疑之外,尚帶出了若干話題﹕
1. 「致命地認真」的「鬥文件的社運」模式,由天星皇后開始,到反高鐵抗爭終於爆發出來。市民自行研究文件(方某也參加過「浪漫」的分判式會議紀錄工作),往往令那些官員和高層啞口無言——因為這些他們自己的文件,他們自己都沒研究過。暴露出他們根本偏袒而不客觀的。
2. 碼頭工人罷工,其實工人自發的(工聯會、勞聯和街工都幫不到手之後才找職工盟),但傳媒仍只著眼於「誰代表工人」而沒理會工人自身。(當然也不用像自由黨膠人般聲稱「工會不要介入工運」,以他的邏輯商會和政黨—包括自由黨—都可以解散掉了。)
碼頭工人和紮鐵工人罷工的分別在何﹖
眾人認為主要在於碼頭工人相對較年輕也懂得IT應用,所以能自我組織(有工人更諷刺說謝謝李超人有股份的網絡和facebook),但紮鐵工人的年紀較高和教育較少,比較依賴工會組織。
不過另一方面,相對於紮鐵工人入行較難、體力要求高、訓練(建造業訓練局師徒制)也不是由商家直接控制,碼頭工人的入行門檻較低,而且訓練都是委諸碼頭本身。所以碼頭主(=李超人)所受的威脅反而不及紮鐵工潮那麼強。
至於碼頭工潮迴響甚大,是否跟李超人本身有關﹖各人看法不一。在下則認為單是因為涉及首富,也足夠是蘋果日報大幅關注的理由了。(反之則很多收取超人集團廣告費的傳媒試圖淡化事件和譴責工人,CCTVB的垃圾節目自是其一。)
(方按﹕當然,紮鐵工運有多「成功」自然也是多有爭議。)
3. IT發達,面書動員與傳統社運方式結合成趨勢,以反國教為顯例。
像零三七一和反國教般,要到「人人都想去」的地步,才有足夠的壓力。
4. 方某順道幫周小姐的《陽光時務》打打廣告,拿其中一篇文章提醒大家留意。只有一班對民主熱心的人,但香港有那麼多「經濟人」,如果無法找到簡單又吸引一般的理由(如法國大革命的「麵包」),是無法令整個社會支持或同情運動,這樣很容易失敗。
戴耀廷的「協商日」究竟除了「圍內協商」還有甚麼作用﹖參與其中的人表示還有其他用途,medium is message(媒介即訊息)。理論武器需要準備,但「入屋」論述是會有的。
希望如此。
---
下次想要討論甚麼題目﹖歡迎到讀書會的page發表意見。
(廣告﹕網上博物館節目日曆已更新了歷史博物館和海防博物館的講座資料,但因為未收到歷史博物館通訊、網頁又未更新,未能添加展覽資料,稍後才能完成更新。非歷史博物館屬下各館的資料已上載。)
 《司法覆核與良好管治》戴耀廷,香港﹕中華,2012
《司法覆核與良好管治》戴耀廷,香港﹕中華,2012
(配樂﹕法の女神—《HERO》電影版插曲)(播放完畢)
為學校買的,不過似乎除了我之外沒人看,所以在圖書館放了半年後終於借回來讀了。
(當然這也不能說假公濟私,因為這本書對於教通識科法治部分是有用的,只是沒人借。如果我認為對教學沒幫助學生又不會看的,就自己買算了。這本我認為放在圖書館比自己收藏更有用,遲點有相關爭議就可以推介了。)
之前介紹過戴耀廷的兩本書,所以本文不再重複介紹戴。
這裡的忠實看倌應該知道在下為何會看這本書。不純為對法律和規章的興趣,而是因為當年在代表會三位一體之後,其他人推舉當代表會主席也不要,專注搞章,結果閉門造車搞了個「中大法庭」出來,然後又因為「缺乏諮詢」為由收起來。
回想聽從大家的話去管理行政可能比較好(而且CV更好看),雖然「中大法庭」也留了給後人很多聯想,但始終沒人去跟進。在收回當時,方某就反省了問題是因為「太大想頭」意圖一次解決所有事,結果甚麼都解決不了。其實代表會裡最大的司法問題,就是對委員會決定的上訴,所以搞好這些上訴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根本暫時不需要試圖去解決那次未見過的問題(既然未見過,亦不見得能提出好方案)。於是臨落任之前寫了份《行政上訴附則》的稿,把問題縮窄到上訴就簡單得多,希望後人跟進起來容易一點。(當然,正如上述,直到現在都沒人搞,這是後話。)
所謂的「行政上訴」,其實很類似司法覆核,那份附則稿裡就順便包括了。(如果認為司法覆核也太複雜的話,我甚至認為把它先剔除也可以,只搞上訴,日後有需要再補上。其實在學生會搞行政上訴,最重要不外乎是規定聆訊小組組成、迴避利益衝突、和規定要詳細交待判決理由而已,而最後一點尤其重要,可免代表會重新審議時人多嘴雜理念不清。)
既然如此,方某對司法覆核這回事一直保持興趣,就不是難以理解的事。
本書的內容,書名其實就得很清楚,所以不需要長篇介紹。內容就是分門別類介紹司法覆核的法律基礎、相關概念和程序,和近年發展的評論囉。
與一般的法律書籍相比,本書有一個明顯的優點,就是案例都選自本港。通常法律書討論到案例大都是英國的經典案例,作者選取本地案例,對一般讀者來說會更切合本地需要、更易理解。
如果大家還記得當年居港權案後中共震怒的反應,就會知道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指法庭積極介入社會事務,借判例推廣其觀點、改革政治之類)頗為中共所忌,龐大威脅之下終審法院竟然要出一份聲明確認尊重人大的權力。
在這種壓力下,近年香港法院傾向消極,只檢查行政決定的合法性(更不用說現在包致金退休、司法機構由保守法官主導的情勢)。作者提醒大家的就是,司法覆核並不止於制止違法的行政決定,它還可以透過檢查行政機關的決定,推動良好管治(善治、good governance),這並不代表就要侵犯行政機關的權力。
在一個不夠民主的社會,法院對社會發展可以有更大的作用。
當然現實可能是,在足夠民主的社會,法院才有更大的周旋餘地。
總是以為香港有「自由」就夠的人們,漠視了「民主」、「自由」和「法治」其實是互相支持,缺其一則其餘難保。
當年英治下無民主而有自由和法治,只是因為港英政府背後,是倫敦的民選政府而已。現在特區政府背後的政權是甚麼本質﹖大家都很清楚,那又何必心存僥倖﹖以為沒有民主還可以保得住自由和法治﹖
(方某人的其他書評與書介)
[宋代近世財政國家的形成]
由科大的劉光臨教授主講。
不知是否因為近來「中港矛盾」炒得正熱的緣故,出身河南的劉教授,在正式開講之前,介紹了自己的背景,然後說認為自己也是香港人,同樣支持民主普選云云,就差在「香港話」還說得不好。
(噢,除非要跟廣府話作對照,否則在下也很少用「香港話」這種說法呢。)
個人覺得講座內容不算很有組織,不過聽起來也算有趣。同樣用點列算了。
1. 在講者讀大學的時代,提到宋代大家都只歸納為三冗﹕冗官、冗兵、冗政,雖然文化商業都興盛,卻承受不斷打敗仗的民族恥辱。到後來在外面留學,才改變了看法。
講者認為對宋朝的負面評價,其實是到近現代中國面對外國侵略時,回望歷史而產生的觀感。
2. 現在大概只有共產黨還堅持「技術是歷史原動力」的馬克思主義史觀,但這種觀念已經落後,反而往往是制度和組織的需要催生了技術發展。
正如香港相對於大陸還有優勢,並不在於技術(大陸的各種技術已大有進步),而是在制度。李超人建立的商業帝國,也是得益於香港制度上的鼓勵和保護。(方按﹕即所謂「地產霸權」,是制度上對地產商的傾斜)
那麼這個「制度優勢」是否「民主」﹖現時西方社會都是民主政體,可是香港卻是自由而不民主(相對台灣而言)。在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散佈民主潮流之後,西方也是到二十世紀才開始穩定地實行民主。英國雖於十九世紀成為霸權,但福利主義和人權概念都是在二十世紀才普遍施行。
民主對於我們來說,除了是一套制度,還是一種道德理想的追求。與古人對「儒家聖人」的追求相對,都要看是否能落實。
香港「制度優勢」另一個類似的例子就是「上海租界」,這些外國殖民的據點,把各種西方先進事物和思想都引進中國。於是我們又要追尋「殖民主義」的由來。這個「現代化西方」是從哪裡來的呢﹖最後,我們找到宋朝原來已有類似近代的「財政國家」。
3. 在這裡,既然要考究制度,我們要先討論一下「好政府」的定義。
是否像一些人所說﹕管得越少越好﹖可是,現代公認的「好」政府通常也管得很多。
例如英國尤其是個大政府,他們曾經有最大的海軍,稅收也很重(相對於陸軍而言海軍是特別花錢的)。英國有歐洲第一個官僚政府,其實這是從中國學來的。(方按﹕類似科舉的「考試取官」首先又是香港開始學—即政務官前身的「官學生」,然後散佈到印度和英國本土。)
英國其實也實行了很多社會主義的措施,反而在香港實行更原始的自由資本主義。
一般而言,一個「好政府」是一個有能力的政府、能夠支持經濟發展、提供公共服務(如維持秩序,這點李超人也代替不了政府)。當中產生了正反饋﹕政府支持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又增加了稅收。
在這方面,西方和日本學者首先發現,宋朝擁有歷史上第一個「成功」的政府和制度。
3.1 宋朝是第一個依賴募兵制的國家。於是政府可要求應召者符合某些標準,而宋仁宗時(即是包青天時)已有百萬兵。
3.2 宋朝是第一個把稅收貨幣化的國家。(而非像之前的朝代依賴徵收實物)
3.3 宋朝是第一個有效的中央集權國家,中央政府派員控制了稅收。
這一點非常重要。正如現在大家對朱鎔基最大的印象就是「反貪」,但其實他反貪不成功,任內官員貪污反而更嚴重了。朱鎔基最重要的是,改革開放原先令地方政府富起來尾大不掉,朱的稅政改革重新讓中央政府掌握了財政,令國庫發達了。朱的稅政改革提升了國稅局的地位,收集到很多錢,於是可以用來做各種安撫和「維穩」的工作,鞏固了中央政府。
宋朝就已經有「國稅局」(方按﹕我想他指的是三司使吧,有篇文章認為三司使也是歸中書管),反而到後來的朝代就沒有了。
3.4 宋代首次把官位全部公開競爭(即科舉)。
與明清不同,宋朝考中進士也只不過是到地方出任稅務官,三甲才可以從通判做起,然後慢慢提拔。不如明清兩朝中了進士就要獨當一面的。
宋代之所以多「冗官」,就是因為建立了大政府,要高薪養廉,又要官僚互相監視。
3.5 宋朝還以判例逐漸改變法律,以適應社會需要。(方按﹕其實後來也是這樣,開國時代的律法通常到後來就被判例改變,《大清律例》就是例證。)
宋朝的法律還特別保護私有財產。
保護私有財產,是為了解決「擁有權」的問題。在這裡宋人「講義理」和「講錢」並不矛盾。因為就是愛講錢才更需要道德,藉以證明自己是「依法」而且「理應」得到那筆錢。
當時判錢債案,還要考慮利息和通漲問題。
而且判決對借還媒介也要分清楚,例如借的是銅錢就應該用銅錢還,想用交子/會子(紙幣,宋朝另一世界級發明)還錢的話就要計算折換率。(情況就如現在用外幣還款要計算匯率一樣)
公認才情橫溢的蘇東坡在官府也要負責放債,大儒朱熹也要負責收消費稅。在那個年代並不是甚麼矛盾的事。
3.6 宋朝亦是首先以法律保障遷徙自由的國家。
我們慣常稱讚的漢唐兩朝,雖然威武,但都嚴格控制人身自由。因為經濟和稅收都未貨幣化、亦非市場經濟,所有事情都以戶口為準,例如抽壯丁參軍。
講者指史學界向來認為政府聲明有兩大笑話﹕
一是聲稱「自古就是中國領土」﹔
二是聲稱「中國人民愛和平」——中國人民或許愛和平,但政府顯然殘暴得多,要不然何來超越中原,有那麼大的國家﹖
在政府眼裡,國家發展首為征戰,所以法家強調愚民,不准百姓太多享受,以免消磨鬥志。(毛澤東後來貫徹這點,不讓百姓有好日子過。)
隋唐兩朝,都不是純粹的漢人朝代,而是胡人和漢人的二元統治。皇族本身就是混血,道德上也不全依中原那套。而且是以胡人治漢人,絲路商人主要是突厥人(當時向西亞學習)而沒甚麼漢人,打仗也是以少數民族或混血兒領軍。
講者認為清朝處理新彊西藏,就比共產黨做得好。因為滿清本身就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又有與其他少數民族結盟的豐富經驗,他們很明顯少數民族的心理,便於駕馭。
相對而言,漢人缺乏胡人的「英雄氣」,比較依賴制度(如科舉考試)。
(講者說這有點像現代西方社會。我想倒不全然,西方人雖重制度,但「英雄主義」氣息亦重。更不要說美國人連年征戰,倒不如說是順便當練兵。)
可是,在唐朝這個國家之內,兩種不同的人是無法同場競爭的。要考試麼﹖胡人考不過。鬥「勇武」麼﹖漢人又拗不過。
唐朝和平之下江南士族(漢人)逐漸興起,而少數民族(胡人)亦逐漸不服唐朝統治,於是唐朝就崩潰了。之後的五代十國,展開了一場制度競爭。
3.7 宋代也是首先以量化方式考核官員。(有如今日的GDP評核)
之前說了,宋朝進士易考,但三甲才從通判做起。宋朝官制出名複雜、官又多。莫說皇親國戚不任實官,就是「官親」升官也不容易,很多人都只得到虛銜(如在某部門掛名有如顧問)而未有實權。
求升遷者多,宋朝乾脆把所有的因素—甚至是你有甚麼背景後台—都統統納入「計分」了。(跟宋明理學家帶來的印象不同,宋代一般很承認「人欲」。)(方按﹕你看趙匡胤竟然想出杯酒釋兵權就知道,用名利贖回兵權、避免誅殺功臣,歷朝僅見。)
「舉薦」既然可以加分,那麼如果升官者後來品行不端施政有誤,舉薦人自然也有責任,自己要扣分。(講者說現在中共就是欠了這個,推薦人不負責任。)
施政方面,由於人民自由流動,所以戶口數目不代表甚麼,納稅戶增長才可以加分。同理,稅收增長也可以加分。而地方官另一重點﹕判案結果有多少人上訴,也會影響分數。
於是,宋朝官場可以說是「人人有希望,個個沒把握」。
4. 講者從五代十國的制度競爭扯到英格蘭銀行。(方某這筆記調動了次序。又,如果有讀過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應會對討論英格蘭銀行和股份制一段有印象。)
英格蘭銀行的成立,並不是甚麼資本主義的成果,反而是因為威廉三世為了跟法國打仗,但當時各種稅項(包括佔了一半份額的特殊稅如啤酒稅等)都不夠用。於是威廉三世和瑪莉王后共同出資帶頭成立英格蘭銀行,是為了發債籌錢打仗的。
同樣地,宋朝也是依賴特殊稅多於田賦,所以鼓勵移民到城市。
例如酒稅,城市的酒家乾脆由政府壟斷,偏僻各處的就交付民營。原本是以「拍賣」的方式競投,以承諾提供最大稅收者得到牌照。後來發現拍賣價太高,很多人交不起就在交稅限期前「走佬」,找擔保人也無濟於事。於是又改為「入標」方式,讓競投者出「暗標」以免瘋狂競價。
5. 宋代的重商主義,實由內戰分裂的制度競爭而起。
原本搶掠富商的軍隊,發現長久下去要官商合作才能安定繁榮。
因應用兵需要任人唯親的政府,也發現長遠治國要依靠制度和讀書人。
講者說了個多小時,那個 powerpoint 一直沒動,現在終於啟動了。看到就知道為何不用開,因為那個 powerpoint 是出國講學用的,跟今天講座的內容並不直接對應。
不過其中一張簡報就引起在下注意,因為那張表格列出了宋朝稅收的分佈情況。只是很快就跳過了——其實您不如一開始就停在這一張然後開講吧﹖
表格顯示,宋朝大概有32%的稅收是專利稅(如酒稅),另外約三成是土地稅。這就是宋朝有多依賴商業貿易的例證。
因此,宋朝大開運河,其實就等於今天政府建高鐵和高速公路,都是為了方便營商多收稅。而且宋朝也鼓勵集中經營、作坊大型化。對於官員來說,向一個大富商收稅顯然比起向很多小市民收稅容易得多了。
另一幅圖顯示當時的弓箭武器。宋朝的禁軍大部分原來是「弓兵」。就是因為宋人怕死、戰鬥力差,所以力圖以技術補救。
相對起來,鴉片戰爭時的清朝,整體而言並不窮於英國。但科技落後,西方因為各國交戰,科技日益進步,而清朝固步自封,於是英人攻來之時自然戰敗。
6. 這樣說,難道就是「經濟決定論」嗎﹖
與一般人認為「稅收多少決定了政府可以做甚麼」不同,徵多少稅其實是政府決定的。(方按﹕當然我想他的意思不是指政府可以不理現實情況胡亂徵稅,而是指政府制度本身決定了它有能力徵到多少稅。)
現代社會「大政府」徵稅頗多,西方一般都有GDP的兩成。問題不是徵稅多少,而是徵稅如何用於民生。
一般而言,與同時代的西方各比,中國歷朝徵稅還是比較輕的。
中國在洋務運動時、日本同樣開始了明治維新,可是日本徵稅徵得更徹底。當日本向清酒徵稅時,清朝官員卻認為「我朝向來不徵酒稅」。稅收的分別對國家實力有很大影響。
7. 問題時間,有人問那麼宋朝為何滅亡。
教授答,現在研究可知,宋朝一年的貨幣供應量,多於明朝近三百年的總貨幣供應。
由此可知,宋朝絕非亡於經濟問題,而是亡於「北京的帝國主義」。
中國周邊的遊牧民族,並非我們所想的那麼「邊緣」,他們實際上是佔據了亞洲的中心位置。這些遊牧民族通常比較重視大帝國和土地,多於經濟和知識。這是他所說的「北京的帝國主義」。
制度本身需要符合人性和社會習慣。
而制度之優劣,視乎你的對手是誰。
相對於范仲淹的全盤失敗和王安石的部分成功而言,蔡京的改革是宋朝最成功(雖然他號為奸相),但那時代的宋人太自滿了。
又有人問,宋朝是否被冗官拖垮了﹖
教授認為,官多或腐敗並不等於王朝就會滅亡。正如後來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政府也很腐敗,但反而越來越強。(當然他們後來就要打擊腐敗了)
亡國多是因為軍事失敗,國民黨就是例子。就算說國民黨腐敗,當時國民黨能夠掌握到的財源也很有限,但打敗了仗自然就沒機會去實踐。
還有人質疑,為何教授在講座中稱毛澤東為「英雄」,因為在香港人印象中毛澤東是壞人。
(我認為這問題純屬誤會,說毛是英雄並不是稱讚他「好人」,是指他「英雄主義」、「魅力型領袖」之類。因為他原來說的「英雄」是與成吉思汗之類並論的。)
教授解釋,他所謂「英雄」是指以一人之力逆社會潮流、改變所有人的生活。毛澤東是最徹底的「英雄」,他說所有農民要交出土地、財產吃大鍋飯就做到,說大學教授和學生不該留在大學要去耕田就把他們都趕到鄉下。諸如此類都是非常人所欲,但他有能力使所有人跟他的意思做,這就是「英雄」。
很多人(甚至毛自己也認為)說毛澤東是「皇帝」,其實毛根本不是皇帝。中國有哪個皇帝可以像毛澤東那樣把民眾任意舞弄的﹖大鍋飯、大躍進、上山下鄉這類事,有哪個皇帝夠膽做﹖如果有皇帝敢這樣做,也可能立即被趕下台了。
與毛澤東相比,史太林算不算是這種「英雄」﹖似乎有點疑惑。
至於希特拉,他的「英雄」也只是徹底改變了猶太人的命運而已。只有毛澤東那麼徹底。
---
有一點教授沒提到的,就是如果宋朝已經成為一個「財政國家」,那麼即是應該做到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了,那又何以會輸給北方民族﹖(北方遊牧民族是機動的,不需要數目字管理)
如果以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論,他認為宋朝未做到「數目字管理」的,證據是連樞密院和戶部的帳目都未能一致。當時有很多商業發達的跡象,但很多事業還是官府操使未能放諸民營,而且未能令全國標準一致。
或者應該說,宋朝是有財政國家或數目字管理的芻形,但歷史上不幸遇上金人和蒙古而滅亡,後來的朝代又因為中國彊土太大難以劃一而重新退縮到道德治國小農經濟(用另一角度看就是農業中國蓋過海洋中國),這種體制沒機會發展下去吧。
另外找到有篇文章質疑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理論。
很久沒逛書店,星期五晚去了,自然又買了一批。有些自己要,有些給圖書館。
(自己買四本,比圖書館那五本更貴……)
 《失控的正面思考》Barbara Ehrenreich 著,高紫文譯,台北﹕左岸,2012
《失控的正面思考》Barbara Ehrenreich 著,高紫文譯,台北﹕左岸,2012
Johncoal 大也撰文推薦了,向來視「正能量」為另類邪教的在下,能不買一本放在學校警惕眾人嗎﹖
 《爸爸媽媽上戰場》國民教育家庭關注組著,香港﹕天窗,2013
《爸爸媽媽上戰場》國民教育家庭關注組著,香港﹕天窗,2013
為何要買這本書放在學校,你明白的。
 《我愛韓國古裝劇》西家雲雀著,蕭雲菁譯,臺灣東販,2013
《我愛韓國古裝劇》西家雲雀著,蕭雲菁譯,臺灣東販,2013
為何會買這本放在學校,單看封面不解釋看倌應該也很容易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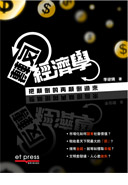 《反轉經濟學—把顛倒的再顛倒過來》李逆熵,香港﹕經濟日報,2013
《反轉經濟學—把顛倒的再顛倒過來》李逆熵,香港﹕經濟日報,2013
身為擁躉,有新書不買不成。
不過這本絕不藏私,直接放到圖書館。因為香港被市場原教旨毒害已久(噢,翻這本書才發現這個詞又是別人先想到的),經濟學好像就只是那一套。所以更有必要讓學生看到現在的主流經濟學有何缺失,而經濟學還有哪些可能。
 《錢穆講中國經濟史》葉龍,香港﹕商務,2013
《錢穆講中國經濟史》葉龍,香港﹕商務,2013
方某曾介紹葉龍兩本錢穆「中國經濟史」的聽講筆記,還有本以人物為本的《歷代人物經濟故事》。有朋友說壹出版不再出歷史書了,也許因為這樣這本書給商務出版了。
因為我猜學校有用,所以買回圖書館,但其實自己也想讀。因為歷史書講帝王將相的多,甚至講方某喜歡的制度史亦有不少,反而講一般生活的不多。當然經濟史不是沒有,正如史書往往也有貨殖篇,但通常不是最吸引人、最多人討論的範疇。這些生計問題,往往才是王朝和時代的基礎。
 《法治—英國首席大法官如是說》Tom Bingham 著,陳雅晴譯,香港﹕商務,2013
《法治—英國首席大法官如是說》Tom Bingham 著,陳雅晴譯,香港﹕商務,2013
英國大法官討論甚麼是法治,在這時候讀這種書還需要解釋嗎﹖
這本書還相當緊貼時代,就像是反恐和法治的關係都討論到。有很多問題不是傳統法治討論覆蓋到,有需要看看更新的討論。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 著,吳國卿、鄧伯宸譯,新北﹕衛城,2013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 著,吳國卿、鄧伯宸譯,新北﹕衛城,2013
首先在哪裡看見介紹呢﹖朋友﹖《陽光時務》﹖
推介文說像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槍炮、病菌與鋼鐵》,我想到的反而是另一本《新國富論》。因為《新國富論》其實也是分析為何國家會成功和失敗。
 《法醫.屍體.解剖室﹕犯罪搜查216問》D. P. Lyle 著,蔡承志譯,台北﹕麥田,2013
《法醫.屍體.解剖室﹕犯罪搜查216問》D. P. Lyle 著,蔡承志譯,台北﹕麥田,2013
簡單點說,整本書就是問「這樣做是否可以殺死人」或者「這樣被殺的人是否能測得出來」這類聽起來「引人犯罪」的問題。
其實有點後悔。
倒不是後悔買了(還未讀後甚麼悔),而是後悔把它當成「自己的書」買了而非放在圖書館。
因為學校(要滿足政府)的無謂會計規矩,買學校用的東西是不應該用信用卡的。於是雖然老媽很喜歡用信用卡儲積分(方某從來不要信用卡),但買學校的書就不能用。所以跟老媽一起的話,就要在很短時間內把要買的東西,分成「自用」或「公用」,然後分開結帳。
倉促之間,我覺得這本書內容有點「變態」,似乎比較適合留給自己看。可是後來我也覺得這些正經得來又「變態」的內容,應該很受學生歡迎……
(倒不因為怕被人投訴,畢竟其實如果你了解法證多一點的話,可能更不想犯法。因為曾有法證人員—好像在《科學人》見到的—這樣說﹕你越是想洗刷掩飾犯罪證據,就越有機會留下另一些證據。
正如為何偵探小說多「密室殺人」,就是因為密室殺人雖然在讀者眼中「好詭異」,但其實容易寫、甚至容易查。如果有個人在鬧市街頭突然倒地身亡,你反而難找出誰是兇手呢。)
 《漢字樹:從圖像解開「人」的奧妙》廖文豪,台北﹕遠流,2012
《漢字樹:從圖像解開「人」的奧妙》廖文豪,台北﹕遠流,2012
貓頭鷹的老貓社長推了幾次。整本書都是討論漢字字源字義,相當有趣。(而且寫的人不是修中文而是修電腦的)
其實還有《漢字樹2﹕人體器官所衍生的漢字地圖》,不過書店未見到。
[家陣老笠]
電視新聞講北韓,老媽說不明白為何還要援助這種國家,讓他們有更多資源搞核彈。
我﹕他們就是拿核彈威脅你給援助嘛。他們就是寧願餓死人也要搞核彈,好敲詐你們。
老媽﹕問題就是為何還要給資源這種國家,讓他可以繼續搞核彈嘛。他可以有多少核彈﹖打起來一定輸的呀。
我﹕他會輸是必然,問題是正常國家都會怕被攻擊、要死人嘛。就算他只是打一堆普通炮彈,南韓都立即會死很多人啦。
情況就像遇上打劫,妳會不會這樣跟賊人說﹖
「我係唔畀錢架啦,你都係得一把刀之嘛,頂多咪插我一野﹖我先唔會畀錢你去買多幾把刀﹗」
(雖然情感上我完全同意,這種國家應該讓它滅亡,就像它西面那個「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的友邦一樣。)
(後話﹕其實 Arnold 有篇〈如何協助有核武的飢餓國家〉)
-------------------
[出口轉內銷之大字報欄]
@區家麟 潮池﹕自由行在中大
我反而對那張大字報的內容有興趣,因為我認識的「組織死老鬼」大多歡迎直選。
不知道近年是否有新規矩,不過我很懷疑第一點是否成立。因為中大學生會會章向有「代表一經派出,未經代表會同意,不得撤回」的保護條款。理論上書院學生會可以委任自己喜歡的人,但一旦委任後他們投票違背書院學生會意願,你也沒他辦法。你連彈劾他也要中大代表會同意才成。所以嚴格而言,「沒制衡」這一點無論委任直選,都沒分別。
(老實說,如果代表委任後,要服從書院學生會的意見,那其實也很恐怖。因為這樣他們就不能以中大學生會的整體角度去做決定了。)
不過我倒同意第二點的憂慮。如果投身直選同學不多,書院學生會也不能委任代表補充的話,那麼代表會的工作肯定會受很大影響。不過我認為這影響中大代表會本身,多過影響甚麼「書院學生會代表權」。
(當然反過來說,委任制度存在也是很少人參與直選的因素之一。既然沒人參選我就可以等書院學生會委任,那又何必辛苦去直選呢﹖我讀書的年代也只有一個曾當幹事的同學,後來去直選當代表,其他人都是等委任的。等書院學生會開會雖然麻煩,但總比參選簡單得多。)
第三點更說不通。既然直選代表也是以書院為單位選出的,那麼他們自然亦應該在制度中被視為「代表書院學生觀點」的人,怎可能只有書院學生會壟斷這一點﹖如果連直選的代表都不能代表書院學生,那麼只是隨院系會選舉內閣順便產生的院代系代又真的能代表書院學生﹖
—三十中代表會章主 (當然代表身份也是被委任的)
坐巴士回家,遇著一個阿叔一個阿嬸,不停在大聲說話,十分煩厭。
更煩的是,他們講政治……
……
一直在聽他們講甚麼希望習近平真的「打老虎」呀、像包青天般掃清毒奶粉呀……聽得頭幾乎撞上玻璃窗。
到廿一世紀,中國人還是在「望明君」,這不就是中國人折墮到今天的原因﹖
如果你們也懂得說那些官員人在江湖不得不貪,即是你們明白貪污的結構性。那麼習近平打不打「老虎」真的重要嗎﹖(假借反貪整肅異己這點我姑且不談)
「殺一儆百」﹖如果整個官場都令人不得不貪(他們自己說的),那麼「殺一」甚至「殺百」又有甚麼用﹖千千萬萬的官就會不貪了嗎﹖
(更不要說,習近平本人難道就不是在這個「官場」之中﹖)
更慘的是,阿嬸還扯到「成龍沒說錯,中國人果然要管」。你現在講的是中國「官」要管呀﹗怎麼變成中國「人」要管呢﹖
「中國人要管」,唯一的結果就是記者被國保打,不是那些官被管了。
為何我們人民還是那麼漿糊腦袋﹖
既然說得出貪污有結構性,為何就不能再推一步,想想這個結構是怎樣來的﹖怎樣去消減/消滅它﹖
一百個明君、一千個包青天,都殺不盡貪官。哪個「個人」有能力去監視所有官員﹖
如果官員只向上級負責而不向人民負責,那麼只要上級沒留意(或者縱容),他就可以為所欲為。
「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後蜀主孟昶官箴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
只有自由的人民、自由的傳媒可以無時無刻監視所有官員。
只有官員向人民負責,才能令他們行事時有所忌憚。只有「官不聊生」,才可避免「民不聊生」。
人民有權力才能制衡權貴,其實也不見得真的顛覆了權貴。只是既然你有票在手,他們瓜分利益時總不敢不留少許給你而已。如果你沒票,他們就連那小點也可以吃掉,留給你做好心麼﹖
為何同樣是共產黨的爪牙,民建聯在香港要派「蛇齋餅糉」,大陸的共幹就不會﹖不就是因為你手上有一票﹗那一票只是選個權小責輕的議員,那麼你當然就只得「蛇齋餅糉」的份量了。
當然我不是說「只要有民主,好事自然來」。民主自由國家有貪腐的也不少,只是通常沒誇張到中國的地步。(因為很快就會被傳媒發現炮轟了)
在民主體制中,人民還是有保護權力的必要。正如政客一樣,你不守住自己的權力,就會失去。
就像上一次說,民主健全的國家,人民遇事並不只指望別人,而是自己組織起來去解決、去爭取。
只有人人留心社會,人人起來負責,這樣民主政體才有生命力。
有時刻留意的公民社會,官員才不敢鬆懈。
(舉個例,你以為常常要去開中大校友評議會那些章則會,真的很好玩很得閒麼﹖就算對章則有興趣也用不著去煩自己—尤其我最憎過海。
不就是因為先前見到他們亂來實在太震驚,為免再受嚇不如自己坐進去。就算未必阻止到他們,至少算盡了力。)
「望明君」之大誤,正是人民放棄自己行動,而旨望有個「救世主」出手解決一切的懶惰思維。
既然人民懶得主事,那麼結果自然就是被人擺佈、被他人主宰。
等而下之的,就是自己不起來爭取權利,還要對其他反抗者嗤之以鼻,認為他們只是「搞搞震」阻住自己做奴隸。
阿嬸說甚麼「終於明白為何『來生不做中國人』」,抱著這種思維,給你們去到外國,不也是把外國變成中國一樣﹖
……
為何阿叔阿嬸沒法多推一步,想到不要貪官、不要毒奶粉的根本,就是在於人民要勇於爭取權力、要勤於參與公事﹖
別忘記了,香港之有今日,也不過因為被英國人移植了一點無根基的法治。要不是有這段歷史,今天搶外國奶粉的,就是你和我。
你不去保護它、發展它的話,日後你的際遇就會跟大陸的人一樣——當然不是像他們那麼暴發了,而是隨便被驅趕殺戮、隨時剝削一切。
你以為有廉政公署就不會回到六十年代的日子﹖別傻吧。
Recent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