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放學,監管完一批學生完成閱讀報告後,就跑到教協會所拿學生的好書龍虎榜獎狀。
根據我收到的傳真,有一份書評優異獎和一份讀後感推薦獎。但職員找來找去卻只找到兩張推薦獎獎狀。
因為正常而言,每間參賽學校都會有兩份讀後感推薦獎(初中高中各一),所以很明顯是我收漏了一張推薦獎傳真通知,而他們放漏了一張優異獎獎狀。
於是我唯有等他們找到那張獎狀再來取。走進教協田園,想望望是否有關於反高鐵的新書賣。
反高鐵那本找不著,論八十後的倒有(林匡正的《八十後運動》,當然也跟反高鐵有關,奇在次文化堂網頁全無介紹)。
更驚訝/感動的是﹕
我在書架上竟然還見到兩本《吹水無邊》……
我應該感謝書店捧場不下架,還是為他們未能清貨而歉疚﹖
於是我又買了幾本書。
-------------
星期五明報副刊有篇健吾的文章(關於香港書獎,我想說的是……),討論日本和香港的書獎操作,裡面有這樣一段﹕
有得到書獎的作者私底下跟我說﹕「現在書已經沒有市場,文學書就更是市場毒藥中的毒藥,作品只要得到香港書獎,或是什麼中學生十本好書,那些從來都不看書的圖書館管理員就會大手入貨,自然會賣400至800本。你看看李智良的《房間》,根本是一本好書,但是就是在得獎後,他才賣,也不過是賣2000本。那麼,你說是不是市場兵家必爭之地﹖」
另一方面,我剛在教協田園買的《香港閱讀現場》中,看到台灣人這樣說﹕
在香港政府推動語文課程改革與閱讀的作為中,最讓台灣中小學羨慕的,應該是讓每個學校都配備「專職」的圖書館主任。(p.56)
「我們認為一個全職的圖書館主任,對學校十分重要。圖書館主任要肩負資訊及媒體專才、教學夥伴、課程改革促進者,及教與學資源的統籌人等新的角色及使命。」教育局陳嘉琪博士指出。
從二零零一年開始,教育局要求學校必須從現有教師隊伍中,找出專職的圖書館主任,不用兼任何其他課程。從二零零一到二零零四年,教育局也舉辦專為圖書館主任設計的在職培訓課程,以及和香港大學合作提供圖書館主任文憑課程,引導圖書館教師裝備專業,推動並支援「透過閱讀學習」的教改核心。(p.57-58)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圖書館主任還不讀書,好像是十惡不赦。
但這不是事實。
首先,圖書館主任並非專職。
教育局的要求,「理論上」的確是要一個專職、全職的圖書館主任。可是事實上,像書中介紹那位除了圖書館課之外沒有其他課節的圖書館主任,在香港也許有如鳳毛麟角。
書中提及那個課程,二零零四年後仍有辦,在下也有參加。在下的同學當中,有位小學圖書館主任有三十節課要教,而且沒有圖書館助理。你可以估算一下她還有多少時間留給圖書館,又或者估算一下那間圖書館還有多少時間可以開放。
方某比較幸運,學校沒給我太多教節、而且有一位助理幫忙。做事總算較有「閒情」,不至於疲於奔命。絕大部分的圖書館主任都有課節,幸運一點的只上圖書館課,但大部分都要負責其他科目的教學。而大部分圖書館主任都教語文科,備課改簿需要很多時間可想而知。究竟有多少時間留給圖書館,全視乎校長是否看重圖書館。
這個現實很明顯跟教育局告訴台灣人的理論很不同,因為教育局其實從沒要求學校「只」讓圖書館主任做圖書館工作的,否則就不會有上述那位兼三十節課的同工了。
(當然,如果一所學校有三十班,而每班每周都有一節圖書館課,那麼圖書館主任一樣有三十節課。但我認識的那位同工可不是開三十節圖書館課喔。)
教育局講那些甚麼「課程改革促進者、教與學資源統籌人」之類的東西,我們聽了很多。圖書館主任協會的前會長經常開玩笑說﹕教改文件裡編派給圖書館主任的工作,按項目計不單多於其他老師,甚至比校長更多。(當然這是因為圖書館主任的工作比校長具體,所以容易分別列舉。)
但事實上,教育局編給圖書館主任的職級在全體老師中是最低一級。(CM文憑教席,理論上不用讀過大學也可以當,學校裡通常有幾個CM職位。CM有機會升到的最高級是SAM高級助理教席,頂薪級等於GM學位教席的頂薪點。)
當然,如果校方倚重(通常再加一些圖書館以外的工作給你)的話,可以把圖書館主任轉為GM學位教席,那麼你就不用爭升職也可以有較高的頂薪點。我甚至知道有圖書館主任是SGM高級學位教席(要兼任升學及就業主任),但真正有這待遇的圖書館主任應該不多。(我沒有數字,但對於學校而言,既然教育局說你是CM也可以就沒必要給你較高的)
更搞笑的是,教育局把圖書館寫得那麼「偉大」,又是否真的那麼重視圖書館主任呢﹖
前陣子教師語文基準試風波時,曾有教育高官安撫老師們,說「如果基準試不及格的話也不用辭退,就轉去當圖書館主任好了」,把圖書館說成是教師庇護所,引來圖書館主任協會炮轟。
給圖書館主任最低職級、考基準試不及格就去圖書館,你說在教育局眼中,圖書館主任有多「重要」﹖有多「專業」﹖
教上述課程,現已回了澳洲的 Henry 教授常抱不平,說要求一個低級職員去「統籌」全校的閱讀活動和課程改革並不合理——誰要聽你的話﹖圖書館主任應該當成晉升職位云云……這是後話。
其次,圖書館主任的職責並不是看書。雖然有很多人(包括一些校長和教師)都以為圖書館主任的工作是看書。
世上可不是沒有負責「看書」的圖書館員,不過肯定不是中學圖書館主任。《圖書館的故事》的作者,就是一個負責「評鑑」的圖書館員,大學圖書館請他來檢視圖書,看看有甚麼值得特別保留、甚麼可以丟掉的。很明顯中學不會有這種差事,而且這種事也不是每個圖書館員都做得來。
學校圖書館主任的主要職責,是負責圖書館日常工作的營運和監督(甚至看管學生…)、教導學生學習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和統籌學校閱讀活動和推廣,是一個「行政」偏重的職務。
當然,這樣不是說圖書館主任不需要/不應該看書。圖書館主任當然以愛書為佳,就算是一個普通老師亦應該多看書。在下亦不諱言,大概真的有一些圖書館主任很少看書,正如一些老師一樣。
某書商經常分科整理書單、再加上少許推介詞,彩色粉紙印刷寄給各科主任做推廣。畢竟不是每個科主任都會經常留意書市的、更不會像方某般逐本書略看過才買,這種服務對繁忙的老師實在太方便。所以有不少科主任記起需要「消化」購書預算時,往往就會照單光顧。
這樣其實很易買到不適合的書(庫大也中過招,但敝校也買了同一本),不過卻是招徠生意的好點子。有些中大校友開二樓書店來詢時我也轉告過。雖然,如果你本錢不多的話很難這樣做就是了,所以他們最後也走了另一條路,看來似乎也辦得不錯。
根據對那書商的購書經驗,只能說,推介圖書其實不能亂來的。但對著科主任填報的書單,同樣未看過那些書的我,也說不上甚麼。
但如果因此像健吾(所認識的作家)說圖書館主任不看書,只靠書獎名單購書,那是不公平的。
因為就算圖書館主任是愛書人,也不代表真的可以不依靠書單。
方某自認愛書,連書評也刊成書了,但看了多少書﹖入行以來,試過有些年看了六十本,有些年十幾本。但相比於全年出版過的書,算得上甚麼﹖
何況每個人興趣有別,看的書都不同。就算方某讀書較雜,對於文學、藝術之類的書還是不大了了,以致曾有人質疑﹕「圖書館主任可以不看《哈里波特》的嗎﹖」(為何一定要﹖學生讀甚麼我就追著讀,那麼我還有時間讀其他書嗎﹖)
去年的好書龍虎榜,曾有記者向在下詢問,在下碰巧讀過幾本,其餘的也要加點力「吹水」應付過去。今年的好書龍虎榜一拿上手,竟然一本都沒讀過(要記得方某的標準,是一本書由頭到尾讀一次才算數,「掃」過的不算讀過)。只有幾本我略略「掃」過幾段。
連在下也遇上「書單中一本未讀」的情境,難道那是因為我不看書嗎﹖
要依靠書單買書,根本不是因為圖書館主任不看書(當然也有這種人),而是因為書海太大,任何一個圖書館員都不可能兼顧。
就是在外國更「專業」的圖書館員,也要依靠種種工具選書的,書獎名單是其中一種。外國同工比較幸運的是,他們書市發達,圖書館界也較發達,於是還有很多選書工具,例如有專供圖書館員訂閱、介紹新書的期刊,甚至有新書評介的年鑑。這些東西香港有嗎﹖
在香港當圖書館員,能夠依靠的選書工具其實極少,書獎名單幾乎是唯一的工具。至少,「名家推薦」就算馬虎,被推介的書大概也不差,圖書館員跟著買進就沒錯。如果不看書獎,就等於完全要靠自己去逐本看逐本選。學校圖書館一年購書,沒一千也有幾百本,一個圖書館主任有多少時間留給圖書館,這樣選書要多少時間才做得完﹖
於我而言,就是香港書獎和好書龍虎榜的書,也不會全部買的,覺得學生不會看、老師又用不著的還是不買。不過至少我不用懷疑它們是否適合學生看、不用太勞神去察看就是。
圖書館員看書永遠是好事,多看書可以培養選書眼光和觸覺,不過這取代不到書獎的參考作用。我要說的就是這樣。
對圖書館員有要求沒有錯,不過也請看看實際上有甚麼限制。
 《男人的上半身去哪了》(專頁)
《男人的上半身去哪了》(專頁) 。雖然從來沒想過「只是玩玩下」,但根本也從沒處理好人際關係的複雜面吧﹖
。雖然從來沒想過「只是玩玩下」,但根本也從沒處理好人際關係的複雜面吧﹖ 。作者說「為何男人親老媽多於老婆」我沒法置評,不過他最後告誡女士們親媽媽的男士還是比較好那一段,我覺得可圈可點﹕
。作者說「為何男人親老媽多於老婆」我沒法置評,不過他最後告誡女士們親媽媽的男士還是比較好那一段,我覺得可圈可點﹕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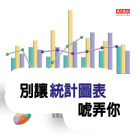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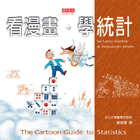
 《
《 (
( (
(
Recent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