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台長遇上歷史學家]
八月尾的講座,因為開學實在太忙,要檢查的資料又多,一直拖到現在才寫好。
(更多照片在後,不想聽講座內容的看倌可直接「飛」去尾。)
---
顧名思義,由現任台長岑生主講的講座。由於裡面提及的圖片部分在樓上的天文台130周年展覽也出現過,所以嘗試穿插在內容之中。其餘照片我會放在後面。
岑生一開始,先講自己是聖保羅書院的舊生。目的有二﹕
其一,會考時他曾經問校長「不考歷史可不可﹖」,但不知道校長就是教歷史的。(結果當然不可 
 )
)
其二,副校長原來也是教歷史的,不過當年沒教過他。反而是當上台長要研究台史,才找上他。
第一部分
台長嘗試找一些天文台最早期的照片。
上海徐家匯天文台比天文台早11年開台(1872)。
徐家匯藏有一張1930年4月28日上海、青島、東沙(﹗)等地代表到香港開「東亞氣象局長會議」的照片,對香港來說算是很難得。後來香港方面翻查,的確發現相同的照片。
天文台現存最早的相,分別攝於1908(由大包米拍攝天文台遠景,諾士佛臺的一排樓是標記)和1913年(總部大樓,走廊有個人影被傳為當年台長但未能證實)。不過距離1883開台年份始終有點遠,所以才想找到更早期的照片。
於是台長開始在拍賣網站物色,買到一張照片,在一個英文網站 Gwulo: old Hong Kong (台長依仗,這個網站還會多次出現)中竟然有網友指出曾有人在1906年寄出的明信片背後有這照片的影像。台長再以相中景物與1902-1903年的地圖對照,的確看得出左手邊的地磁儀建築。
然後又找到張1923年颱風襲港的明信片,照片是彌敦道(美麗華酒店對面,即是天文台附近),畫面上有塌樹、電話線桿都被吹到扭曲,而畫面中央的長木椅還有「Ladies and children only」的字樣。
同一場颱風的另一張明信片,有沉船、當中還有一隻英國L9潛艇。
(在澳洲國家圖書館的 Trove digital newspaper 資料庫可找到當年的新聞報導,文字描述與明信片內容相當吻合。)
另外一張1906年颱風塌樹的明信片,同樣是被網民查到背後有人寫了資料。
之前的照片都是幾百元一張,但一張由港島望向九龍(因此拍到天文台)的照片卻買了二千。因為從照片中未完工(還有棚架)的香港會會所,可推斷照片攝於1896-97年間。
另一張有1897-1898年的港島海旁(當然也是遠望九龍),照片特色包括拍攝到添馬艦、中環填海、和雪廠街碼頭(天星碼頭前身)。
一張1886年照片的複製本,拍攝到天文台旁邊地磁站的外貌。
舊台長 Peacock 收藏的舊照片中,有這一張,圓形磚牆就是放赤道儀之處。
這一點甚至在地圖上也看得到。
與英國檔案局的舊地圖比較(即是先前提及的1902-1903地圖)可見,天文台山的左側有地磁儀(magnetic),天文台1883大樓的南邊緊鄰一座赤道儀(Equatorial),大樓尚有一座中星儀(Transit)。
(以前地圖要記得那麼詳細的麼﹖)
後來台長在哈佛大學網頁找到份1885年的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長報告,謂﹕Lee 6-inches equatorial 已送到香港天文台。可證實香港天文台的赤道儀型號。
台長於是「膽粗粗」去信格林威治天文台,問可否找到這部赤道儀,回覆是因為太舊沒用他們已送了給科學館(Astronishing Science Spectacular Museum)。科學館那邊說因為底座爛了,不便遠行,所以暫時都未能安排來港展出。
相片倒有一張﹕
最後一位英籍台長 Peacock 說以前的助理台長 Leonard Starbucks (呢個姓好熟呢 XD) 告訴他放赤道儀的建築是特別為了赤道儀而建,不用赤道儀後就用來放本地風球(標示大陸地區的風球仍在其他地方放)。
可是看更早期的文件,其實未有天文台前,香港已有地磁觀測紀錄,亦有時間球和weather signal (在police hulk掛放),詳情仍待查證。
天文台早期的三大工作,就是授時、地磁觀測、和報天氣。(其實都是為了服務港口航運而設,所以你就明白為何天文台一直都是歸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管的。)
所以台長認為現在已不用的觀星報時或地磁觀測,其照片儀器等都是值得收集保存。
---
第二部分
有待考證的資料。
一張1877-1878年間的海圖。(抄下了,現在才發現自己沒拍過照……)
天文台網站的三吋中星儀照片,為何會跟徐家匯天文台那張中星儀照片幾乎一模一樣﹖
台長曾向徐家匯天文台查證,他們的確有這部儀器,那即是說天文台其實襲用了人家的照片張冠李載了。(台長作驚嚇狀 :O )
開台時的 Chief Assistant (名為台長助理,實質為助理台長) John Isaac Plummer,是來自 Orwell Park Observatory,當時該台使用 Troughton & Simms 75mm transit。可以相信他也會為天文台訂同一款式的中星儀。
台長無意中在收藏家鄭寶鴻先生的著作《香江風月﹕香港早期的風月場所》中,讀到1874年一場颱風影響妓院恩客的記載。於是與鄭先生聯絡,後來在鄭先生身上得到很多掌故資料。例如在未有政府《香港年報》前,華橋日報的《香港年鑑》已有記載當時的颱風資訊。
其中一張舊照片拍攝到當時船政廳(即海事處)懸掛風球的位置,並有1906年風暴中的醫院船,鄭先生說這艘醫院船很少在照片中出現。
在光緒二十年(1894)出版的《香港雜記》記錄了1874年的甲戌風災和1889一場大雨(其三小時雨量紀錄,至今未破)。
1874年的甲戌風災,大概是香港開埠以來第一場大風災,亦直接促成了香港天文台的成立。這場風災對澳門的影響更大,當時澳門只有萬五人口,這場颱風引發的風暴潮卻導致了五千人死亡。
香港大學物理系教授(亦是很多天文台職員的老師) Prof. P. Kevin MacKeown 寫了一本書《Early China Coast Meteorology: The role of Hong Kong》,對香港早年的風災著力甚深。
書中記載,早在1861年香港已有人建議樹立「時間球」(time ball)來代替不太準確的午炮報時。
1874年風災中,香港(只計當時英國殖民地的港九)死了超過二千五百人。沒人認領的遺體被集體埋葬於雞籠灣的「遭風義塚」,直到墳場停用時被遷往和合石。而甲戌風災亦是東華醫院的首次賑災行動。
根據當時《Illustrated London News》(倫敦新聞畫報)的報導,當時海水倒灌市區達四呎深度,海堤亦被沖毀。
1900-11-10 的庚子風災是另一場傷亡慘重的風災。報導這場風災的西報,背後那頁就是八軍聯軍入京的新聞。
台長特別指出引述這場風災,認為足以說明公眾對天文台的誤會﹕
—有如近年大家「李氏力場」的調侃,這場風災正是在夜間侵襲,到第二天早上八時,香港已風平浪靜。可是只掛了三個小時的「十號波」(當時未有這系統,純屬比喻),卻死了二百人。所以不要以為天文台半夜掛風球是跟大家開玩笑。
—而且,這一場風災並不涉及天文台失誤,天文台已提供了足夠的預警時間。只是因為大家都認為「十一月哪會打風」,所以沒理會警告。
—更有甚者,港督卜公的報告指出,這年夏天時天文台曾放過風炮,但最後發現是誤報。現在也有很多人聲稱寧願風力不足也要先掛風球,其實多掛了「不夠力」的風球,只會令市民疏於防範(於是我們就見到大家八號風球照常上街飲茶的景象),當真正的威脅來到時傷亡就更慘重了。
方某在小時候聽老媽說過一個傳說,說有一任天文台台長,因為未能預報一個「返轉頭」的颱風導致死了很多人,引咎吞槍自殺云云。這件事在天文台的「官史」是完全找不著的。
究竟這段是「都市傳說」還是天文台的「黑歷史」﹖
結果這次台長也拿這個故事作引子,不過是介紹1906年的丙午風災。
這場風災之所以令人想起那個故事,是因為這場風災似乎真的令台長引咎辭職。(倒不是自殺)
關於這次風災,有一份官方報告。某天有古董商通知台長,網上正以六千元叫價求售,正當台長在「嫌貴」和「重要文件」之間未能決定,轉眼間就被人買走了。後來經海事博物館前館長 Dr. Stephen Davids 才找到一份複本(﹖)。
有一張明信片的背後,有日文寫著「二時間內」(兩小時內)。這場颱風範圍非常小、幾乎無法預警,當日早上八時放風炮,颱風立即來襲,到上午十一時就吹完,但死了三千人,還包括香港聖公會的主教(當時他正在帶聖保羅的學生乘船去屯門)。
不過死了主教還不是最嚴重,最麻煩的是有艘法國魚雷艇(Fronde)在香港,連同船上軍官一起被打沉了。

由於首任台長跟徐家匯的耶穌會會士不和,風災後耶穌會士隨即表示「我們兩天前已警告了你們」,意指香港天文台預報不力。風災變成外交事件,最後在加士居道現在女拔萃書院的位置建了個方尖碑作紀念,碑石後來移置跑馬地香港墳場。
由於事涉徐家匯天文台,岑生曾在徐家匯查曉當時的氣象紀錄。結果竟然發現風災前的兩份天氣圖「不知何故」神隱掉……而兩天前的天氣圖只見到香港附近有個小型低風壓,完全看不出會是一場颱風。徐家匯在風災當天早上十時發出的天氣圖是這樣的﹕
這幅已是「賊過興兵」而沒有任何預報意義了。如果看倌像天文台批評的那些應徵者「連香港在地圖哪裡也指不出」的話,留意圖下側等壓線最密的地方就是了。千萬別以為是畫中心像箭靶圓心那兩個大紅圈呀,那是山東的高氣壓。(事實是連天文台之友的義工也解錯了,把那兩個奪目的紅圈當成了颱風的暴風圈。如果暴風圈有那麼大的話,天文台事前都不知道,台長恐怕就真的要吞槍自殺了。)
港督就此事向倫敦交報告,內容為台長辯解。因為當日天文台吹十一級風,
六十公里遠的澳門卻只吹一級風,可見暴風圈小得離奇,根本難以預報,直到當日早上7:44都是「no indication of typhoon
approaching Hong Kong」(沒有颱風襲港的任何跡象)。而當時亦有 amateur meteorologist
投書報館為天文台辯護,說沒可能預知得到。(台長笑言一百年前也有氣象迷,只是矛頭跟2006年剛好相反)
因為港督的報告,天文台長並沒有被責罰。不過大抵是因為這件事帶來的壓力太大,所以在翌年,台長就以55歲之齡提早退休了。
另外一場是1937年的丁丑風災,香港開埠以來死人最多的風災。台長找到這張海報,這是一個當年在金鐘海軍船塢做工,後來回英國終老者的後人提供的,據說這張海報當時就是掛在船塢內的。
一場颱風會印製海報,現在你也沒聽見有這回事吧﹖可想而知這場颱風對當時的人有多震撼。這張海報紀錄了當日的氣壓、潮高、沉沒/擱淺船隻的名字和位置等。
這場颱風造成的破壞包括﹕
—中環潮水有 13 呎 (正常潮水為七呎六吋)、水浸至德輔道、(當時的)郵政總局地庫也水浸
—彌敦道也有水浸
—有小魚被吹到 20 呎高
—大埔有漁村颱風後完全消失了(人自然也…),傳說有 18 呎的風暴潮 (數字很誇張但無法證實)
—九廣鐵路因為地基被沖毀而中斷了十天
跟2008年黑格比帶來的風暴潮比較,當時大澳水浸有半個人高,鰂魚涌則有 3.5 米的風暴潮。
香港風暴潮紀錄中,以1962年溫黛在大浦滘的 3.2 m 為第一名,其餘的我抄不及了,第五名是1979年荷貝的 3.23 m。
丁丑風災的風暴潮傳為 3.8 m,丙午則為 6.10 m,不過都是未能證實。
台長找到「一個旅行家的日記」,是當年一個四處遊歷者的記錄和照片,當中也有丁丑風災的記錄。他拍了一隻船的照片,說鄰近的這隻船隻因為失控,船上的人怕沉船就在十號風球之下跳船逃生。在方某眼中似乎比留在船上更危險,而那隻船最終撞上岸擱淺。
這本日記很貴(過萬元),因為裡面也包括很多香港和鄰近地區的歷史照片,所以台長就情商歷史博物館購藏了。
當時的台長 Charle W. Jeffies 分析了 1937 和 1936 年兩個路徑極之相似的颱風。1936年那次香港未成災,只是因為它的路徑偏南幾十公里而已。
丁丑風災的風速紀錄為 167 mph、約 269 km/h。當時天文台的風速計早就爆了錶,所以這個紀錄是港燈北角發電廠的測風站數據,而且還因為技術問題(據聞風速到頂就不準)而要加上 3 mph。
這位台長的任期為1932-1941,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在任內逝世的台長。死因為中風,葬於香港墳場。英國有位女士在網上放了香港墳場所有碑石的資料,台長的碑上悼文指他曾擔任國際氣象組織(IMO)的「遠東區委員會主席」。岑台長說這令人很驚喜,因為這幾十年香港天文台的職員最高級都只擔任過分組委員會主席。
(有關香港墳場的研究已成書﹕ Patricia Lim《Forgotten Souls》)
Jeffies 逝世後隨即接任的台長就是其副手 Benjamin Davis Evans (任期 1941-1946),這位台長算是不幸,一坐正就遇上香港淪陷。
(其實同期的不幸者也不少,包括當時的輔政司詹遜,而且這位輔政司是由錫蘭轉到香港一上任,第二天日軍就攻過來。等到重光時又被麥道高架空了,算是十分不幸的遭遇。當時的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也只是淪陷前幾個月才任馬上任。)
岑台長在聖保羅的副校 Mr. Geoffrey Charles Emersons 原來寫了本《Hong Kong Internments 1942-1945》,介紹這段時期在集中營的外國人。
集中營裡其中一個女孩 Barbara Anslow ,現已 94 歲,但為人還相當精靈。岑台長寄電郵去問,即日就覆。當岑台長按書中描述問 Evans 的事,她立即就記起那段日記來(她記下 Evans 常常在集中營天台教大家天文學),如同昨天。
而且她在淪陷當日,被送到旅館軟禁以待送入集中營時,還拍了張照。那間旅館的名稱分別有寫成「Tai Koon / Ta Kuan Hotel」的,其實只不過是等於現在的時鐘酒店。究竟這間酒店在哪個位置﹖鄭寶鴻先生一聽就說,這是大觀酒店嘛﹗就在中環街市附近。(這一段連網上記載附註的地圖也搞錯了,岑台長聽後幫手澄清。)
---
第三部分,叫懸案。
1946-1956年的台長 GSP Heywood,他在深水埗集中營(屬軍方集中營)時用打字機寫日記,戰後釘成一本《It won't be long now - the story of a Japanese prison camp》。文中提及當年天文台職員只有三個是歐洲人(Evans 台長、Heywood 自己、和台長助理 Starbucks—不是現在那間咖啡店﹗),其餘職員都是華人。(換言之,因為其餘人都是華籍,不會被關在集中營)
可是後來的「官史」《From Timeball to Atomic Clock》提及,1944 Mr. Thompson 被關在赤柱集中營時,有人在紀錄雨量。這是誰﹖是否有其他人被關在另一集中營﹖這暫時是未解之謎。
(Heywood 女兒就在這本書封底的天文台職員合照中亮相。)
近年天文台獲得意外收穫。就是從神戶大學的塚原東吾教授那邊,得知有一批日軍戰時在華南的天氣檔案﹕《南支那氣象概報》
看倌可見到其中一張蓋上「用濟後燒卻」的印章,可見是軍事機密。正因如此,這些檔案亦殘缺不完,塚原教授暫時只找到其中一個月的檔案。日後或者可以找到更多。
天文台的顧問邱文廣教授,現年67歲。著名氣象學教科書《A Short Course in Cloud Physics》的作者 Rogers and Yau 的 Yau 就是他。
原來他當年考完預科後,在20歲時進入天文台擔任科學助理,兩年後就去了外國繼續升學了。1966年美國新聞署的《今日世界》就訪問他,因為他為香港皇家天文台發明了「超土炮」的衛星訊號接收裝置。這個裝置被美國報紙說成「香港人用垃圾打敗了我們﹗」
因為當時氣象衛星是新發明,可以自動追蹤的天線裝置動輒要百萬美元(當時屬鉅資),當年的邱先生竟然在一個舊油桶上支撐一條長天線,「追蹤衛星」就由天文台的工人人手負責﹗ (其實只需要按時轉方向令天線保持正對衛星就行,不過這份差事可想而知悶得要命。)
這套簡陋的「接收裝置」連工人的人工,只需二百元正﹗ 就這樣做到百萬美元所做的事,所以便宜到嚇到美國人。
簡陋成這樣的設備當然不可能接收後,直接安坐椅上就看到衛星影像那麼便宜。邱生要先把衛星訊號用「錄音帶」錄起,然後把磁帶逐條掃瞄成像,再拍照才得到衛星雲圖。(這就是省了百萬美元的代價)
後來天文台購入「濕傳真」機器(據聞早期的傳真要以氨水顯影),才可以把訊號直接轉化為圖像。
不過在戰後資源短缺的時候,面對最新科技,這也是天文台搶先嘗新的事例之一。岑台長認為勇於嘗試也是天文台一貫的特色(例如天文台網頁開得頗早,現在還為國際氣象組織的氣象資訊網頁做 hosting),希望日後能夠保持。
------
除了講座,方某其實早就看了展覽,所以也拍了點照。
展覽入口有個很有趣的模型,模擬在訊號山公園(即大包米)的時間球運作方式。(其實就是下午一時之前,會用電動把大球舉升到最高點,然後到一時正就跌下來,讓海港內的船隻可一起對時。義工說選下午一點的原因是中午時太陽在正中不便觀察云云。現在有這種電動模型真好,當中讀官史的時候只能看著英文自己想像。)
不過更有趣的是,模型是訊號山公園的時間球塔,但背後壁報照片的時間球塔,卻是舊水警總部外的那個(即是現在被首富搞到不似古蹟的1881)。
而且海上的船隻還會動的。
這些是當時的照片﹕(天文台開台後,才接手水警總部的時間球工作)


看倌也可以見到,無論是模型或歷史照片,時間球塔旁邊都掛了一串颱風訊號。
這些訊號是指甚麼﹖其實都是給船隻得知颱風大概在哪個方向、有多強勁的訊號。東亞颱風訊號的具體制度是由徐家匯天文台確定的,香港天文台也是照跟。
台長在徐家匯獲贈一張法文版海報的複製品、也拍攝了英文版的海報,印出來當展覽品。
看倌應該覺得有點面善吧﹖因為現在香港的颱風訊號和符號,也是從這一套演變而來。
不同的訊號象徵了不同時間掛出的訊號(說明了有效期)、不同的方向和風速等。我拍攝了細部,不過恐怕沒時間慢慢參透了。
天文台歷年來的徽號,很多都是沿用英國的皇家徽號(畢竟這是「皇家天文台」)。
下面的是
FitzRoy barometer,發明者正是那個載著達爾文環遊世界,又因為達爾文發表演化論而跟他反臉的那個頑固船長。其人雖然頑固,但可不是沒貢獻的。這個氣壓計可顯示兩天的氣壓和溫度,透過氣壓變化提示天氣變化。
抄說明﹕「天文台根據一八九零年至一九一二年蒐集的數據,於一九二五年編製及出版這本以地圖顯示南海每月平均氣壓、風向及風速的專著,是研究早期南海氣候的重要文獻。」
抄說明﹕「一九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上午六時的天氣圖,是香港天文台現存最早的天氣圖。」
抄說明﹕「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颱風溫黛襲港時的天氣圖。天文台在溫黛吹襲期間曾懸掛十號颱風訊號,破壞範圍遍及市區和郊區,釀成超過一百八十人死亡或失踪,數千人無家可歸,是二次大戰後吹襲香港最嚴重的風災。」
抄說明﹕「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香港雨量分佈圖。這場暴雨引致嚴重山泥傾瀉及大廈倒塌,死亡人數接近一百五十人,促使港府於一九七七年成立土力工程處,並推出山泥傾瀉警告。」
抄說明﹕「《低空風切變探測系統》於一九八一年出版,由天文台職員鍾國棟及崔家聲先生撰寫,記載香港首個風切變探測系統。」(方按﹕鍾國棟其實是台長 Gordon Bell 的譯名,有趣吧﹖)
下圖是系統使用的多普勒雷達。
抄說明﹕「啟德機場氣象所曾使用的風向及風速表刻度盤。該儀器用來顯示跑道東南端(三十一號跑道)的風向(左邊刻度盤)及風速(右邊刻度盤)。」
五十至六十年代電車公司使用的布幅,由於當年未有海底隧道,渡輪停航消息對市民非常重要。(大家可見,賽馬也跟渡輪停航同等重要…… XD)
三十至四十年代的颱風訊號表和全港颱風訊號站位置表。
(大家可見,當時訊號與今日的主要分別,是八號風球當時仍稱五至八號,後來才因為市民會誤以為風速有別而統一。三號風球在當時亦分為二號和三號,分別代表西南和東南強風。東南強風代表颱風應在香港以南,通常稍後香港風勢會較強。另外有個表示「風勢危險但未靠近本港」的四號風球,現已取消。)
最後一個颱風訊號站在長洲,亦於二零零二年取消了。
颱風訊號桅桿的模樣﹕
 《法醫.屍體.解剖室:犯罪搜查216問》(More forensics and fiction: Crime writers morbidly curious questions expertly answered),D. P. Lyle著、蔡承志譯,台北﹕麥田,2013
《法醫.屍體.解剖室:犯罪搜查216問》(More forensics and fiction: Crime writers morbidly curious questions expertly answered),D. P. Lyle著、蔡承志譯,台北﹕麥田,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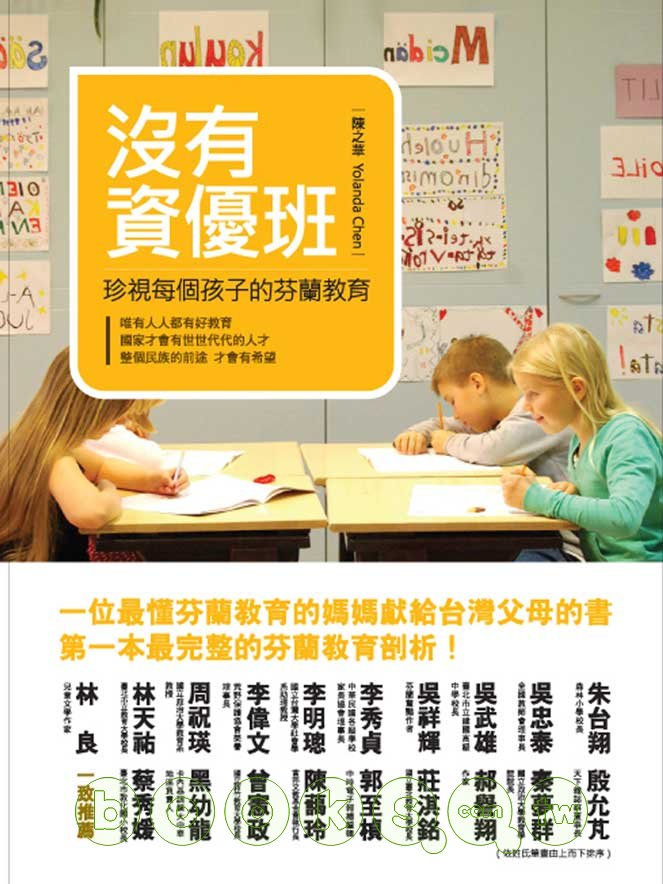






































 《
《
 Dan Ariely《
Dan Ariely《
 Richard Wiseman《
Richard Wiseman《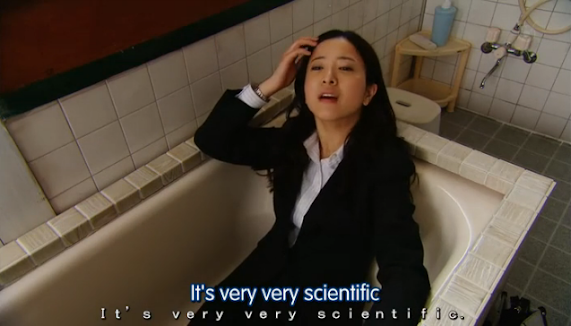 (岸谷@神探伽利略2﹕It's very very scientific)
(岸谷@神探伽利略2﹕It's very very scientific) (岸谷﹕好想知道吧)
(岸谷﹕好想知道吧) (岸谷﹕迫不及待了﹗)
(岸谷﹕迫不及待了﹗)
Recent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