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博客奇文
抱歉,我不打算在這裡評論這篇文(意見放在庫大那邊了)。
只是剛剛看完《鏗鏘集》,見到那些已經被官方壓下來的「追究豆腐渣」聲音,再想起這些「批評政府,不夠客觀」的人,我只會想起余秋雨和「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
既然「做鬼也幸福」,難怪那麼多人要見鬼了。
忍見幼輩成新鬼,中國真是個幸福的國家。
-----------------
其實我想說的是,電視。(看,我多膚淺﹖怎麼看也不像「政治博客」啊﹗)
是呀,病了除了讀書,就是讓自己多看電視。(少開電腦嘛)
星期六下午看了明珠台的《Perfect disaster》,竟然用香港作背景。
說的東西倒不是假(遲早會有超級風暴襲擊香港),不過把三十樓當「高樓大廈」,和香港消防員在女人街叫市民疏散,似乎有點脫離現實。
更有趣的是,片中天文台的「博士」哀求政府官員疏散商業區的人。既然他們也說得出「香港前海後山,無處可疏散」,那麼還要疏散誰呢﹖再者,只要天文台台長(他不一定是「博士」)祭出「八號」,市民就會下班(是否回家倒不清楚),根本不需要政府再疏散誰。
美國人太不了解香港了。他們構思的情節似乎把香港當成美國中西部的小城市。
與其怕香港官員不讓市民疏散,不如怕香港市民「放八號風球假」就四處走(甚至帶小朋友去「看風」),不知被超級颱風吹到哪裡去吧﹖﹗
---
到夜晚,再看《明日之後》。(據聞內地譯成「後天」,我還以為是笑話,但竟然是真的,真陰公)
科學原理(融冰影響大西洋溫鹽洋流,導致冰河重臨)大致是真的,只是過程極端戲劇化。(我很難理解為何寒流會變出一堆像熱帶氣旋的東東,反氣旋和氣旋是兩回事來的)
冰河幾周內重臨,當然是誇張。不過原來事實也不見得慢很多。
之前在《最衰者生存》就提過,我們原來以為冰河和間冰期(即溫暖期)要幾千幾萬年轉換,後來改為幾十年,怎料現在發現原來可以十年之內就完成了。
十年當然比幾周長很多,但這種轉變也只是一代人以內的事,不能說不快。
(如果說紐約在十年後埋在冰下,當然沒十日後般「災難」,但也夠麻煩的)
這其實點出了氣象研究的一個罩門﹕決定性混沌。方程式是決定性,但結果是混沌的。
就算全球暖化完全為真,但融了冰川,竟然可能截斷洋流,導致冰河時期重臨。這在一般人眼中,豈非自相矛盾﹖
但這就是「混沌」,正如我們有一堆氣象學方程,但永遠不肯定風眼在哪裡登陸一樣。只要大氣有少許擾亂,就可能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由直趨香港去了海南島。
正兄說他願意接受天文台的天氣預測,但不願意接受台長的環保聲稱(針對「沒有冬天」這一點)。
我倒是奇怪,如果你接受同一套學問預測天氣,為何不接受它預測氣候。
又一補充﹕以往電腦模式說全球暖化增加颱風數目和威力。
最近有研究說,颱風的數目可能不增加、甚至減少,但威力會進一步加強。
我們是否又當這是廢話﹖
正兄說要反對「環保原教旨」,這點我並無異議。我之前亦多次指出,深綠分子搞的只是新宗教,不是科學。
但我們拒絕了深綠,淺綠呢﹖
姑勿論「零冬天」是真是假(畢竟只有歷史能證明一切),但忽視這些預測,對我們有何好處﹖
又,正兄文中說《絕望真相》有九大謬誤,其實我先前亦有引文。高爾的說法固然有誇張和出錯之處,但法官也承認基礎是符合科學的。如果把高爾當成純粹胡說八道,這也只是「市場原教旨」的反誣而已。
至於「九大錯處」中水平面上升是否千年後才出現這一點,我更相信未必如此。近年南極和各地冰川融化的狀況已越見嚴重(科學人報道
一、
二、
三),去年南極冰棚崩解(
零八年三月號),今年
西北航道也開通了,科學家亦憂慮會失去阻擋後方冰川的「塞子」,會令冰川入海速度加快。這些因素先前都沒考慮過,如果加入考慮的話,水平面上升可能大幅加速——當然,未必是幾年內的事,但不等於可以忽視。
近年我們新增的知識,是「越來越恐怖」而不是「越看越沒事」。
這才是林超英大唱「遲早無冬天」的背景。
當然,替台長下個註腳﹕如果竟然像電影般觸發冰河重臨,又作別論。(這點恐怕沒哪個電腦模式可以預計)
不過,如果遇上冰河期,那又比全球發燒好嗎﹖
如果高爾真是錯,海平面上升是百年後的事,是否代表我們今天甚麼都不用做﹖不用理﹖
如果我們拒絕「深綠原教旨」那些不近人情的主張,是否代表我們不用做其他事﹖
是呀,科學家永遠都不確定,天文台不可能肯定寒冬會消失。那是不是不需要說話﹖不需要去警告大家﹖
如果答案乃「不是」的話,我不明白正兄由反深綠擴大到反台長,對大家有何好處。
《生而為人》有一個很有趣的說法,作者說(大意如此)﹕如果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超越某個閾值,人眼就會把天氣看成紫色,那麼人類肯定會把溫室氣體減排視為頭等大事。
可惜,我們的眼睛沒演化成這樣。人類的感官其實很狹隘、很不可靠,很多事情都無法輕易看到。就像世界漁業一樣,我們直到漁獲大跌後才發現自己捕魚過多,很多問題我們都要等到災難降臨才知道。在見到災變之前,我們就繼續衝過去,直到衝過了臨界點而不自知。
這就是我們需要科學的理由。
又像《大崩壞》不斷引述不同文明的衰壞過程一樣。有人問﹕他們砍下最後一棵樹時會怎樣想﹖
其實環境破壞是逐漸的,而人的記憶總是在適應環境。到最後一棵樹被砍的時候,那些人早已忘記那裡本來有森林了。
沒有超級颱風,香港人就以為打風只是放假玩樂良機,一點都不可怕。只因為他們忘記了溫黛。
台長可能算錯,香港還有寒冬,但我們可能會忘記,原來天氣曾經溫和過。
隨著華南的用水壓力逐漸增加,日後我們也可能反過來被迫記住﹕原來香港會制水。
是呀﹗科學家永遠都不確定。是呀﹗我也反對深綠不近人情。
但我們應該做的,是按照現時所得的知識,去討論怎樣「合乎人情」去實行環保,以避免最可怕的結局。
而不是把科學界的估計,視為危言聳聽,然後繼續當沒事發生過般生活。
醫生說你膽固醇過高、可能會爆血管,你不一定要吃素、也不一定要吃貴價降膽固醇藥,但也應該想想是否要自控一下,而不是說「高膽固醇飲食不一定導致高血膽固醇,血膽固醇高不等於會爆血管」就當沒事繼續大魚大肉。
不吃得清淡點,頂多你死﹔不想辦法搞環保,你可能要大家一起死。
單是這一點就有「迫」你的理由。當然,我還是認為研究採用「合乎人性」的方式推行環保(例如經濟誘因),總比強迫或說教更有效。
但問題不是搞不搞,是怎樣搞。
----------------
再答魚頭小姐﹕妳想我討論《神探伽利略》的哪部分呢﹖
看了兩集,有如教育電視般畫出腸。第二集一開始就猜到是海市蜃樓(不過要等見到爛膠鞋才肯定是因為液態氮),教授也做了一次示範,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呢﹖
(今集蹲在鐵筒上寫算式還說得通,因為知道折射率的話就可以做計算。)
今集最抵死是﹕男主角罵女主角「你見過有人任何時候都鹹濕架咩﹖……你以為教授就唔會睇AV咩﹖」
其實我都係覺得,呢套戲睇湯川學窒人先最好玩。那些所謂「疑團」,沒甚麼大不了的。
P.S. 湯川學實驗室的名牌寫著「補教授」,日文維基百科也沒記載,他的職級是甚麼﹖
(日文維基只載「准教授」,等同於 Association Professor,香港稱「副教授」。)
如果根據一份文部科學省中央教育審議會2005年的討論資料,「教授補」似乎是 Assistant Professor 的建議譯名之一。見另一份詳細討論。
但日文維基以「助教」作為 Assistant Professor 的翻譯。(很明顯跟香港不同,香港的助教只是 Teaching Assistant)
另一份師資名單,「教授補」和「助教授」很明顯並列為兩個職稱。而這一份考試通知裡,「教授補」看來是「助教授」的上一級(所以有助教授資格才可以考那個試)。
至於在東京大學,情況似乎有點亂。如果我們比較地震研究所的兩份職員名錄(日文、英文),則「助教」是 Assistant Professor,應用生化系的職員名錄也是這樣(日文、英文)。
但如果我們看招募廣告,這個助教卻只需要「修士課程修了」(修士即碩士)。
以「教授補」在網站內作搜尋,找到的似乎都只是歷史人物(例如前校長山川健次郎,可惜無法從英文維基對比找出「教授補」是甚麼)。
用最低能的 google 大神比較法,「教授補 associate professor」有1970個日文結果,而「教授補 assistant professor」3190個日文結果。
回到日文維基,他們竟然說湯川學是「准教授」﹗(中文維基當然是照譯成副教授)
除非我眼花,否則這看來也是另一個謎團。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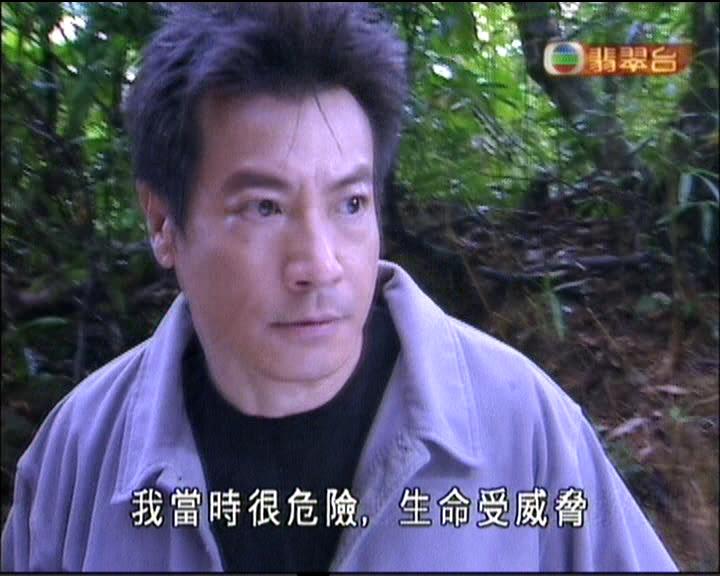 (
(






















 「
「 靜——香港人明白嗎﹖
靜——香港人明白嗎﹖
 雪山飛狐﹗
雪山飛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