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提要﹕庫老大搞了個讀書會。討論以下幾本書﹕



《男女博弈經濟學》王澤基、蘇勇鵬,香港﹕天窗,2012
《經濟自然學》(The Economic Naturalist),Robert H. Frank,台北﹕大塊文化,2008
《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Tim Harford,尤傳莉譯,台北﹕早安財經,2011
前文已提,方某人既然不是修經濟的,所以當然要找些另類門路。所以另外重點推介兩本書﹕


《誰說人是理性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Dan Ariely,台北﹕天下遠見,2008
《紅色皇后—性與人性的演化》,Matt Ridley,台北﹕時報文化,2000
有別於庫大和史兄正式討論(史兄尤其重點表明男女婚配要雙重配合,並非有效率的市場,情場失敗不必然是品質差劣),在下選擇在幾本書中互相比對,找出一些我認為值得討論的地方。
1. 很多時候我們都強調女性重視婚姻(尤其女生迫婚傳聞甚多),好像是婚姻(尤其一夫一妻制)對女性比較有益。當然婚姻對女性也有穩定下來、得到承諾的好處,但其實婚姻(尤其一夫一妻制)對男性的益處更大。幾本不同著作都有提及調查指,結婚對男性的好處較大,而離婚對女性傷害較多。
當年在中大,交功課時欺負老師,面對哲學教授講生物學(同理,向生物教授講歷史),寫了篇學期論文叫《女生為何愛美﹖》,就提及一夫一妻制其實限制了大部分女性分享「富爸爸」資源的機會(情婦畢竟不像妾侍有正式身份)。一夫一妻制實質是保障了大部分男性都有機會得到伴侶(在生育資源上女性是稀缺一方)。
甚至像香港教授的那本,也提到剩女剩男之別在於﹕剩女是有選擇的,只是眼角高所以認為不嫁更好﹔而剩男可能是求一女而不可得。這是男女平等後,女生繼續渴求「向上嫁」帶來自然結果。(當然更不用說﹕男女平等令女性獨身的代價降低,所以女性更有選擇的餘地。)
香港教授的著作,同時亦提到塗指甲對吸引男性無用。這點男性大多同意(雖然後來有男會眾提出塗指甲也有掩飾健康狀況的功效,不過我想以男性的「著目點」而言塗口紅更重要),但女性可能會反駁說「只是為了自己覺得好看」。換言之由「女為悅己者容」演變為「女為悅己而容」。
不過這個可能是拙論文指,一夫一妻制導致女性「種內競爭」(註)激烈,變成要「鬥靚」的結果。
(註﹕嚴格而言「種」是指生物種,男性女性都同屬一種,這裡只是把兩性當成兩個物種來比喻。)
情況就像男人不解的女人「鬥瘦」競爭。本來在古代營養不良,所以有「少少肥」的女性代表健康,男人喜愛。到近現代垃圾食物增加,反而是「變肥容易保瘦難」,所以男人轉為青睞瘦女也為自然。只是男人喜歡的「瘦」還是有少許脂肪,而不是「流行」的那種瘦。如果女性只為吸引男性注意本來不需要瘦成這樣,其實這已變成是女性內部「誰最有能力控制自己體重」的競爭,所以才去到那麼誇張。
2. 《經濟自然學》提及為何「害羞」者得人喜歡,作者認為是因為這代表跟急躁者相比,當事人對自己「估價高」不輕易屈就的訊號。其實我很懷疑這個說法,因為如果換成香港教授的那個例子,就指「長時間失業者比跳槽者更難搵工」,所以建議大家在情場「騎牛搵馬」。那麼究竟害羞帶來好處還是壞處﹖
如果從「港男港女」喜好「食住」對方的心態看,「害羞」的人可能有另一個好處﹕就是他們看來戀愛經驗較少,沒那麼難應付。
3. 方某在讀中國文化科時,辯論「義利之辯」時已認為﹕但凡合義之事長遠必然合利,凡長遠合利之事亦必然合義。
前幾本書很多討論,其實都是局限於一兩次的短期賽局,這樣的賽局近似零和遊戲,其實會鼓勵背叛。如果把它們變成無窮重複的賽局,情況可能就會很不同。這也很可能是人類道德的起源。
想了解人類的行為,除了經濟學,回頭看看生物學家觀察到甚麼,也會很有幫助。畢竟我們很多沒有解決方案的性愛問題,在演化中都被不同物種試了千年萬年。
順道推薦 Matt Ridley 的另一著作﹕《德性起源—人性私利與美善的演化》,台北﹕時報文化,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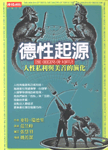
作者討論一般人認為無情和你死我活的演化,為何能夠衍生出道德。
4. 同樣地,《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多次提議用「錢」來解決親人之間的問題。我想如果以行為經濟學觀之,就像 Ariely 說的人類分開 social norm 和 market norm,所以「講錢傷感情」。用錢來解決家務問題未必是好辦法。
不過反過來看,Ariely 同樣提到另一實驗。當要求受試者解答一些麻煩的算術問題,如果即場給現金勝出者,作弊的人未必多﹔但如果改為給代幣,就算在隔壁可以立即兌回現金,作弊率也會大幅增加。那麼家庭內「不講錢」其實是否也會有同樣的效果﹖(例如沒倒垃圾卻說倒了﹖)
5. 香港教授提到「吃回頭草好」,但這個分析(兩人互相熟悉)有沒有計算到兩人分手時已有不少 hard feeling﹖
在這方面,動物可以還理性一點,因為牠們純屬「機械性」。就像一齣動物紀錄片曾拍攝一隻公雀追求雌雀,不停在雌雀面對展示羽毛。過了差不多一分鐘,雌雀無興趣飛走了,剩下公雀「戇居居」失落狀。但牠可能沒甚麼「傷心」,見到下一隻雌雀就會再飛前去做同樣的事。
人類反而多感情,所以才受困於 sunk cost (沉沒成本)。
再者,之前有調查稱在「好朋友」之間,男性往往認為有發展可能,而女性往往認為「沒發展可能」才當朋友。各位又怎樣看﹖
6. 回到「港女」,香港教授說港女是錯誤地把自己定價過高,所以市場失效。但如果我們看行為經濟學的研究,這樣的做法可能是源自「定錨點」的問題。
Ariely 曾在課堂上搞「拍賣」,要求學生標價買一件沒甚麼價值的東西,但起標價是隨機定的。結果發現當起標價高、成交價也高。亦即是說,學生並不是按他們心目中的「真正價值」(如果真的有這回事的話)去競投,「定錨點」對成交價有很大影響。
如果不是港女自覺地採用「定錨點」試圖提高「成交價」,卻搞到市場失效的話,那就可能是整個社會提供了虛假的「定錨點」。因為在香港大眾傳媒和電視劇影響力很大(尤其是二三十年前電視一枝獨秀,沒多少其他娛樂),但肥皂劇的主要對象是主婦(即所謂「師奶劇」),所以內容自然是以討好女性為主。(具體就如年前有套廣告女人可以隨便打男人,如果反過來拍個男人打女人的廣告,婦女團體可能就要示威了。)
香港男女可能就是一直受這些劇集的影響,所以錯誤地把港女「定價」過高。
(有人問為何歐美又不見得是這樣,這個我可不懂得答了。)
7. 最後有個比較容易令人尷尬的話題﹕獻身。
香港教授的著作認為,雖然可以吸引注意,但女人自動獻身是不好的。一則性的邊際效益會越來越低(史兄不同意這個),二則性的可替代性太高、很容易找另一個,並不容易綁住對方,三則男人對性和愛分得比較開,得到了性不一定就有愛。
但如果我們用另一角度看,可能有很不同的結論。
一則,Ariely 曾經研究性興奮對人類(至少男人)決策的影響。在平時受試男性表示不接受的性行為(都是一些較禁忌的事情),在性興奮時就多了人表示接受。既然性興奮令男性的警戒心降低,那麼自然也大有可利用之處。(正如很多以男性為目標廣告都加上性感女郎,就是這個道理)
二則,《經濟自然學》也介紹過「試用」的功效。商家之所以願意提供「用家買了不滿意,N個月內可退回」的保證,正是因為人類通常對自己「擁有」的事物評價較高。如果你已經習慣了那件貨品,覺得不滿退回的機會其實不高(更何況可能嫌退回手續麻煩)。「虛擬」的擁有權也一樣會提高當事人的滿意度。「獻身」是否也可以達到同樣的功效﹖
(當然,女性獻身策略或可綁住好男人,但也有遇上賤男「噍完鬆」的風險。正如美國商家的試用策略,遇上聰明過分的大陸客人就焦頭爛額,曾有報導說有些大陸客喜歡買走一堆衣服,穿厭了就退回來……)
這樣說當然不是鼓勵人隨便「獻身」,只是說決定獻身的女生可能有不同的考慮。
(當然這樣說更不是否認女性也會享受性愛主動求歡,只是這裡女性「獻身」並不是為了「性」本身,所以不用考慮。)
---
後話,Ariely 之後還出了另一本,直接就用行為經濟學討論愛情了﹕ 《不理性的力量:掌握工作、生活與愛情的行為經濟學》Dan Ariely,姜雪影譯,台北﹕天下遠見,2011
《不理性的力量:掌握工作、生活與愛情的行為經濟學》Dan Ariely,姜雪影譯,台北﹕天下遠見,2011
(方某人的其他書介)
 ,不過問答爆笑無減本書趣味,非常值得一讀。
,不過問答爆笑無減本書趣味,非常值得一讀。












 ) RS005 吸塵機,用了多年。替換紙袋 ZR745 剛剛去吉之島也買不到(在網上只找到他們有售了)。吉之島的售貨員介紹另一種替換紙袋,但要先把原吸塵機紙袋的硬卡紙板拆下來留用……我那個袋裡就有一隻(應該未死的)蟑螂,怎可以拆了前面的板……﹖(再不然先隔著袋踩扁牠,然後才拆……)
) RS005 吸塵機,用了多年。替換紙袋 ZR745 剛剛去吉之島也買不到(在網上只找到他們有售了)。吉之島的售貨員介紹另一種替換紙袋,但要先把原吸塵機紙袋的硬卡紙板拆下來留用……我那個袋裡就有一隻(應該未死的)蟑螂,怎可以拆了前面的板……﹖(再不然先隔著袋踩扁牠,然後才拆……)

Recent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