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川博士,或﹕我如何學會停止嘮叨並愛上恐慌]
(大人的不安—《女王的教室》插曲)(播放完畢)
間中聽見有人說李慧玲是「政治八婆」。
我不喜歡這種說法,一直不贊同用這種稱謂貶抑別人。
不過看了今天的《AM730》,我不得不有點同感。
---
自從政府屈服宣佈停課開始,她似乎就把自己當成拯救世人的先知。
「多虧了我大聲疾呼,香港才避過一場疫潮」﹖(設計對白)
姑勿論除了在下,還有其他醫生、從事公共衛生的網友,分別指出今次流感高峰期病患人數不特別多,停課是基於政治決定多於科學決定。
而且周一嶽當時亦很清楚表示,停課是為了讓市民安心,而非因為疫情失控﹕
「鑑於我們數據方面證實流感的數字持續並有少少輕微上升,我們知道流感通常都要數星期才完結,預計流感高峰期尚會持續數個星期;第二方面,我們也看到很多家長、學生和學校亦對此有憂慮。鑑於復活節假期快將開始,所以我們作一個決定,由明天開始,所有小學、特殊學校、幼稚園和及幼兒中心停課……
我們第一方面要看科學的情況是怎樣。我相信市民是希望我們作一些果斷的措施,所以我現在不排除我們現在做的是為謹慎而做的,可能會令一些家長或學生不方便。但我覺得如果我們更加清晰地作這個決定,令學校消除憂心,亦令學校互相感染減低的話,這都是一個有效的措施。我可以說清楚,這個不是一個公共衛生的決定那麼簡單,而是有些看到民情而決定。」(顏色和粗體由本人加上,下同)
再者,今天袁國勇教授發表的報告也跟預期一樣﹕病毒未見毒性加強的變種。
所以我不知道究竟李慧玲憑甚麼以為自己是對的。
今天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曾國輝醫生的說法,更清楚表達了政府的立場﹕
衛生當局由始至終強調,本港流感疫情無異常,兒童流感併發症個案亦不是特別多,那麼當初決定全港小學及幼稚園停課,是否反應過敏?衛生防護中心未有正面回應,只解釋「從科學和普通市民的感覺去看,兩者未必完全一致」。
……曾浩輝則表示,是否有停課需要,可從科學數據和市民本身感覺去看,而從數據上,今年小童流感入院個案不比往年特別高,病毒分析數字雖顯示本港處於流感高峰,但非「歷史高點」。
不過,曾浩輝說從市民角度看,則可能會感到在學校有流感爆發,亦有小童因流感死亡,故市民覺得疫情嚴重而需要停課並不出奇……
之所以要停課,根本就是因為包括李慧玲在內的傳媒,盲目誇大疫情帶動恐慌,聯手迫使政府在科學考量以外作決定。
如果按照李慧玲的邏輯,香港年中也有些小童死於交通意外,「人命關天」,我們應該要求全港學生立即停止乘坐汽車(包括巴士/小巴/的士)回校。亦不應「行街」,免生意外。
(你答我「年年都有人死於交通意外」﹖同理,「年年都有人死於流感」的,值得大驚小怪嗎﹖)
「沙士」時我也不贊成停課(因為沒證據顯示沙士在學校擴散),不過那是前所未見的疫症,所以政府停課也值得諒解。
可是在一個「一年四季都播傷風感冒藥廣告」的城市,竟然因為「流感高峰期」而停課,實在說不過去。(如果真的流感大爆發 pandemic、或學校有禽流感傳染,又另作別論。)
-------------
就胡醫生提及的傳訊問題,又按照「李慧玲邏輯」,我甚至懷疑是否要全港校長強制進修流行病學。因為如果某些校長不是聽不明術語,就是斷章取義不解文意﹕(我希望不會是後者,畢竟貴為校長)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張志鴻認為,教育局的參考指引只能供參考,校長必須視乎學校實際情況。他以所屬的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為例,校內有1000名學生,1%入院才停課,相等於10名學生,反應未免太過遲緩,「有4至5名學生入院已相當嚴重,怎會等到10個學生入院才停課﹖」
教育局發給校長的信,分中學版和小學版,但兩者差不多,我姑且引述中學版的﹕
3.2 若學校裡因相同傳染病及類似的病徵而休病假的人數有上升趨勢或異常(即在同一班內有三位或以上的學生在短時間內相繼出現相類似的病徵),學校應即填妥隨函夾附的「懷疑學校/幼稚園內集體感染傳染病」呈報表格向衛生署中央呈報辦公室(CENO)呈報……以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及防控措施。另把有關呈報表格副本送交所屬的區域教育服務處備存。
4. 若個別學校有流感爆發的情況,本局會與衛生署就有關情況作出個案評估,以決定個別學校應否停課,例如考慮全校有流感徵狀的學生人數、全校因流感入院的學生人數是否超過全校學生總人數百分之一、或有否學童有嚴重流感併發症而在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等。
明明「1%入院」只不過是停課其中一個考慮因素,我真的不明白為何校長會理解為「1%入院才停課」。
(為方便教育界同工理解,試作「學能測驗」題一條﹕
「你阿媽係女人」是否等於「只有你阿媽係女人」﹖)
我擔心的倒不是「1%入院才停課」,而是擔心衛生署有沒有想過「同一班有三位或以上的學生短時間內相繼出現病徵」就呈報調查,究竟會收到多少報告﹖有沒有足夠的人手處理﹖
警戒線不一定越低越好,就像警鐘一樣,over-sensitive 只會令人忽略真正的危險。
當然,「同班三個或以上」已接近「10%」了,作為警戒線也許合理。我只怕衛生署資源不足而忽略了其他疫症。
---
衛生防護中心另外出版了一份較詳盡的「學校預防傳染病指引」,甚至竟然有個「學校應設立感染控制主任……負責統籌及監督傳染病預防及控制的執行情況」的建議。夠誇張的。(這是學校不是醫院喔 ![]() )
)
如果真的要搞,我想若然不是副校長就是實權在手的高層吧﹖畢竟「感染控制」牽連甚大,非權臣任之不可。
不過,我想除了上次的胡說八道外……
我沒有讀流行病學,但倒覺得有一點學校可以留意的,就是請病假人數的趨勢。
如果請病假人數急速上升的話,要求停課也許是有理由的。亦可以比較往年同期的請假數字,就可以知道請假人數是否偏離常態。
還有,究竟請病假的人是分散各級,還是集中於某些班﹖若是後者,校內可能有互相傳染﹔若是前者,當然也不能排除校內傳染,但亦可能是社區傳染來的,停課未必有幫助。
最後還要留意,有沒有病情特別嚴重的學生(例如要住院)﹖他的同學有沒有發病﹖
這些數據不需要等政府,學校管理層大可自行比較,也可以讓老師、家教會代表有參與決定的依據。
似乎還可以為即將被任命的「感染控制主任」提供一些個人看法。
趨勢的分析﹕
1. 最簡單的,自然是看每一天的相對變化,就像股市一樣。但病假人數就跟股市一樣,「可升可跌」。所以要有一條基準作比較用。
2. 「基準」即學校長期(一年或以上)的平均病假人數。根據高人表示,幼稚園的全學平均大概是3%。我猜中小學生比幼稚園學生少病痛,所以應該低一點。(所以才有1%的警戒線﹖在下胡說的)
3. 但既然是「平均」,即是正常也會有時「高於平均」的,所以警戒線應該高一點(+1%???)。例如基準線是1%的話,如果請病假人數是1.1%,也許是正常的,但如果是2%則可能有異。
4. 流感和很多疾病都有高峰期的,所以年中請病假人數說不定也有波動。如果正常波動已經很大的話,則有可能因為自然波動而引起恐慌。所以應該考慮「季節基準」或「浮動基準」。
5. 「季節基準」即是比較現在和上季同期的情況,如果情況差不多,應該是正常的。
「浮動基準」即不只看今天,加上「移動平均線」作比較,更能看出趨勢。我不相信有校長主任不買股票的,所以應該不用解釋了。
但如果學股票看「50天平均線」,似乎太長了。所以我認為用「5天平均線」看一周情況和「30天平均線」看一個月比較好。
6. 亦即是說,學校應該把以往全年的病假數字化為圖表,以「5天/30天平均線」作為「季節基準」。然後就可以比較現時病假數字與以往相比,是否超出正常狀況。同樣一句﹕我不是讀流行病學的,以上純屬個人胡說八道。(或許不比李慧玲好多少
)
(嚴格而言,如果要看趨勢是否明顯超出正常狀況,我想應該還要做 test 看 P-value 之類的參數。不過這些對沒有統計學底子的行政人員而言,似乎太困難了。)
 (
( 《選擇》
《選擇》.jpg) 《國家地理》
《國家地理》 《科學人》
《科學人》 《軍事家》
《軍事家》 《明報月刊》
《明報月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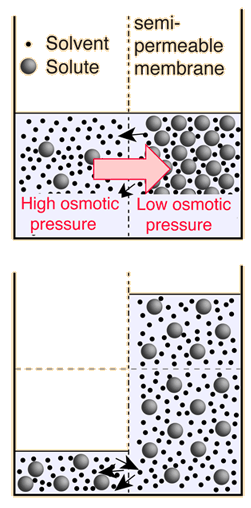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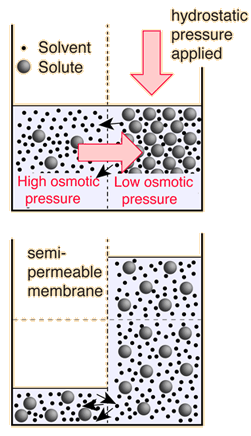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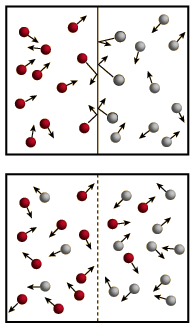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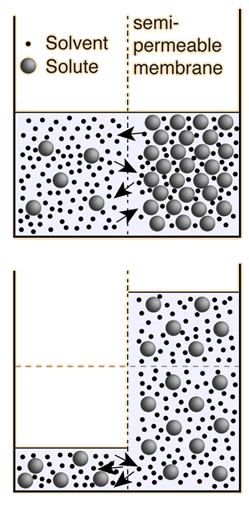 (
( 《
《
Recent Comments